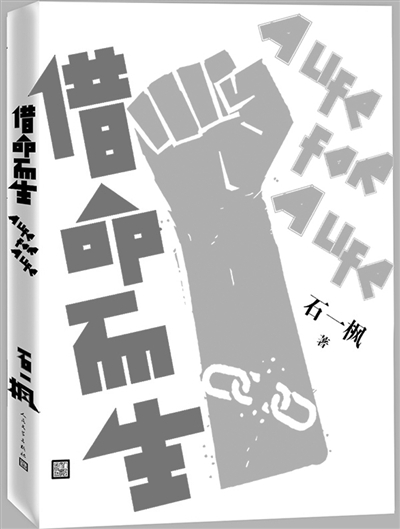|
||||
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所谓六机厂,就是第六机械厂,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北京首当其冲,在城西边建了首钢,东边和南边则依次排开了化工厂、模具厂、火力发电厂……光负责机械制造的就不止一个,按照分工不同,一生二二生三地顺延下去。排到六机厂,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选址在了郊区。而农田和荒野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对于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也有那么一家厂子,是个上万人的锅炉厂,厂里的子弟从小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说话的口音都与他这种本地孩子不同。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杜湘东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愿望,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既偶然又必然,既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 于是他跟着身边的几名工人,不紧不慢地往工厂方向走去。农田尽头耸立着厂房和围墙,越往近处,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亏了这身‘皮’,杜湘东刚一出示证件,说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传达室的人立刻便给保卫科打电话,叫来了那位膀大腰圆的副科长。过了将近一个月,胖子的脸已经养得直冒油光,头上的纱布却不摘,仿佛光荣负伤的瘾还没过够。这人也认得杜湘东,诧异道: “那案子刑警不是调查过了吗,你一狱警又来干吗?” 杜湘东面无表情地告诉对方,第一,他不是狱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还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调查的需要,保卫科都有配合的义务。副科长嘟囔起来,说把犯人送过去那天,该交代的情况不都交代了嘛。杜湘东立刻又纠正:目前案子还没经过法院判决,人也还没正式移交监狱,因此对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称谓就不应该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这就有点存心较真儿了。在那个年代,上述法律常识还不普及,也根本没人会深究,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犯人”地叫,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进来。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种人——你要不当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当回事。 胖子果然肃穆起来,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他给杜湘东沏上了茶,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这才说:“您想了解什么?” 杜湘东直截了当问:“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脚道:“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刑警这么问,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人家没看上我,让我挺没面子,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本来就没挂牢实,我们进去一冲一乱,那铁砣子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不信你问他,我有人证。” 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这是事实。刑事责任,我们也不敢撒谎。” 副科长又说:“我还专门找人问过,这种情况算误伤,误伤就不赖我对吧?”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我又没看清楚,趁势踹了姚斌彬两脚,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花’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吗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怂,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也跟着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专门的术语则称为“鸡奸犯”。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获的。那人刚住进监舍就抗议,说别人要轮奸他,闹得他不敢睡觉;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闹得谁都不敢睡觉。后来只好把这人关到单间里去了。 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都是厂花,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从保卫科出来,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这时却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灰砖的则是筒子楼。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捡着空地上的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11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