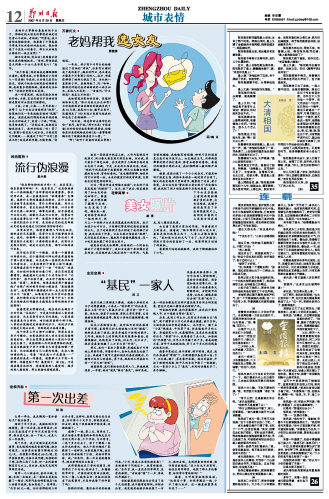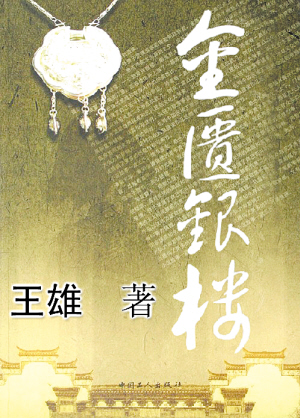|
 |
|
|
|
|||
| 金匮银楼 中原网 日期: 2007-06-29 来源: 郑州日报 |
胡瓜大惊失色:“你这是咋的啦?” “干活失手了。”小武子说得很轻松。 胡瓜不信:“你昨晚不是醉酒了么,干哪门子活?” “我心里烦。” 胡瓜明白了,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手指没了,你日后吃什么?” “饿死了才好呢。” “你,你真是一个混账东西!”说罢,胡瓜浓浓地吐出了一口鲜血,从此卧床不起。 彩凤认定小武子是为她断的指,一个出色的银匠就这样毁了。彩凤在痛惜之余,也深感自己的罪过。 小武子成了残疾人,贾老爷只得安排他给其他的银匠打下手拉风箱。 老银匠胡瓜整天整夜地唉声叹气,在一个天刚破晓的凌晨,他一口气没有上来,带着满腹的伤感和遗憾去了。 55 穿着单衣单裤的二少爷拉开房门,手里挥动着一方洁白的绫汗巾,双眼浮肿地站在卓氏的面前:“娘,嘻嘻,花花巾。” 白绫汗巾上几块血红十分抢眼。 卓氏一把抢过白绫汗巾:“傻儿子,这也是你拿的?” 二少爷扑上来,大声喊着:“花花巾,花花巾!” 卓氏一把将二少爷推倒在床。二少爷躺在床上耍赖,哭喊着:“花花巾,花花巾。” 彩凤与卓氏刀子似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她盯着卓氏手上的白绫汗巾,几块血红很是张牙舞爪很是刺眼。 彩凤十分心酸,不软不硬地问道:“娘,有劳您又来查看‘落红’来了?” “有什么劳?这是做娘的本分呢。”卓氏也挺硬的。 “您昨早不是查看了么?” “昨日让那断指头吓着了,闹心,没看清呢。”卓氏拿着白绫汗巾认真地瞧着。 彩凤斜了卓氏一眼,不卑不亢地说道:“这下子您老可以放心了吧。” 卓氏拿着白绫汗巾看了看,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其实,别看这血红挺打眼的,有时也说不清呢,那金瓶梅里的银瓶嫁给翟员外前,早已是破了身,可银瓶将鸡冠血涂在白绫上就将翟员外哄住了。” 彩凤一脸怒气地盯着卓氏:“娘,您有话就直说,是不是还在怀疑我,说我不贞洁?” 卓氏连连摇头:“不,不是的,我是在说书上的事呢,可惜你一个山里妞没读过书呀,不懂这些。这也不能怪你,你说是不是?” 彩凤红着脸垂着头,眼里噙着泪水,把当儿媳应受的委屈憋在心里。 56 彩凤当二少奶奶了,贾老爷想着要给她压担子。大少爷、二少爷都指望不上,汉皋一天天老了,卓氏的心眼越来越小,惟有彩凤精明可用,这银楼也只能依靠彩凤了。贾老爷叮嘱汉皋,以后银楼里的事多给二少奶奶说说。汉皋问:“太太知道么?” 老爷摇了摇头:“她慢慢就会习惯的。” 彩凤成为二少奶奶,既然是少奶奶就应该有少奶奶的地位和威风,可银楼里的许多眼睛和说话的口气,仍然把她当丫头看。譬如说,苗嫂每日都要问贾老爷卓太太想吃什么菜,可从来不正眼看彩凤。譬如说,一天,前厅来了几位挑选首饰的贵夫人。彩凤正要出门,堂倌来喜竟然对她说,快给客人上茶。 吃鲤鱼是贾老爷多年的爱好。这天,苗嫂向卓氏抱怨,说是市面上鲤鱼不好买,汉江里的鲤鱼几乎绝迹,要到很远的东津镇上去买,只有东津那里的鱼塘里才产鲤鱼。 卓氏说:“每日就雇人去东津买呗。” 苗嫂问:“这多支出的银两咋算?” 卓氏说:“找汉皋从柜上拿。” 过了两天,彩凤找到苗嫂:“太太让我问你一声,这汉江里的鲤鱼果真绝迹了么?”这一问,苗嫂当然明白了,脸憋得通红。 苗嫂自己打了自己两耳光:“都是我贪心,还请二少奶奶多包涵呢。” 彩凤说:“没事的,日后需用钱就直接找我好了。”说着,塞给了苗嫂几块大洋。苗嫂满脸通红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从此,每天一大早苗嫂都要跑到彩凤房里去,问二少奶奶今日想吃什么。这天,苗嫂又来请安,彩凤突然说了句想吃地米菜。地米菜是隆中山里的一种土菜,长在山坡上,只有下雨过后才会有。彩凤只是说说,没想到一天大雨过后,饭桌上真的摆上了地米菜。事后才知,苗嫂一夜没睡跑到隆中山里买来的。 这天中午彩凤转到了银楼前厅。堂倌来喜正趴在柜上打盹,彩凤一把将来喜推醒:“柜里的首饰让贼子偷了呢。”来喜猛地一惊,抬起头来,嘿嘿一笑:“彩凤,不、不,是二少奶奶。” 彩凤脸一沉,突然大声叫道:“账房,来喜困了,让他去屋里睡吧。” 汉皋问:“那谁来站台子?” 彩凤说:“我来替他!” “那……”汉皋仍不解。 彩凤说:“谁站台子,谁拿饷,来喜今日的薪饷就是我的了。”然后转身对来喜说,“你今日若还睡不够,明日就回家去睡。”来喜是乞丐出身,二少奶奶让他回家去睡,显然是让他走人呢。 来喜一听傻眼了,抡起手掌就朝自己脸上打:“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午后,汉皋将来喜的事告诉了贾老爷,老爷哼了哼,算是知道了,竟然没有表态。汉皋试探着说了句:“二少奶奶是不是太张扬了一些?” 没想到老爷眼一瞪:“你认为二少奶奶做错了不是?” 汉皋立即不言语了。 卓氏得知彩凤要辞退来喜是傍晚吃饭时。 多年了,来喜一直在卓氏眼前晃着,卓氏也习惯了使唤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