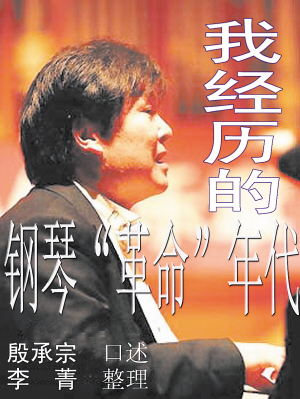|
 |
|
|
|
|||
| 中原网 日期: 2007-11-25 来源: 郑州日报 |
当年,为了让自己钟爱的钢琴不至“灭亡”,殷承宗曾改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使钢琴发出他所理解的“革命”的声音。那些与当时政治气氛高度契合的作品,又使他身由不己地卷入政治风浪,转瞬跌入人生的另一面。 鼓浪屿的童年 我的钢琴之路与很多人不同,12岁前,我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钢琴专业训练。 1941年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那时小岛是外国租界,有12个外国领事馆。我们小时候都在教会小学,听到很多教堂音乐,无形中就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此外,抗战胜利后,很多留美、留英人士回到鼓浪屿,使岛上文化也一度兴旺。他们中不乏音乐爱好者,经常开家庭音乐会,我们小时候都趴着窗子看,有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这样的氛围对我的钢琴之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3岁那年,我的姑夫林文庆——他是被陈嘉庚请来的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离开厦门去新加坡前,把一架钢琴留在我们家里一段时间,我与钢琴的第一次接触是从这时开始的。姐姐们会弹,我也跟着学一点。六七岁临解放时,我的同父异母哥哥从上海去香港,说是把钢琴“暂存”在我们家,但走了以后再也没回来,就这样,我算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钢琴。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童年时父亲的大太太——我的“大妈妈”还在大陆,她很有钱,我替她摆鞋子,她给了我2美元。我用其中1美元跟教堂里牧师的太太学了1个月的琴,另1美元买了给儿童学琴的谱子。我很小就对钢琴感兴趣,小时候听唱片,虽然还不识谱,但我会在钢琴上试着找那些音。我还喜欢即兴演奏,客人来的时候就跑上去表演一段,直弹到被别人轰下来为止。每当高兴或不高兴,都想用钢琴来表达。 一直到9岁之前,我都是自己在摸索。9岁那年,姐姐们想给我开一个独奏音乐会,一是想鼓励我,二是可能也想挣点钱。为此,她们给我找了个老师,算正规教了我几个月。我真的很喜欢,也很用功,把家里的琴弦都弹断了。姐姐一气之下把琴锁起来,中午放学休息,我就跑到人家练。那时我在岛上已经小有名气,9岁能开独奏会的孩子并不多,所以“九龄幼童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手写海报贴出来不久,300多张票一下子就卖光了,这次演奏会的门票一下子把家里9个兄弟姐妹的学费都解决了。演奏会节目单现在还保存着,我当时弹的是舒伯特《小夜曲》、《军队进行曲》;肖邦的圆舞曲;还有我自己编配的《解放区的天》之类的革命歌曲。 周围很多人跟家里人讲,一定要让我走这条路。我也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鼓浪屿。可在那个时代,要走出来,谈何容易?父亲已带着大妈妈去了香港,母亲带着我们9个孩子在内地,姐姐们中学毕业就工作养家。那时我参加了许多社会上的工作,比如在合唱团弹伴奏。厦门音协对我很好,1954年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招生,他们资助了我25块钱学费。 母亲起初不同意,她舍不得我走,我安慰她说“你哭一天就会把我忘了。”于是一个人拿起箱子扭头就走,不敢回头。但一上了船,我就先大哭起来。 那时候厦门还是前线,台湾的飞机经常飞过来,一炸就十几个小时,我们小时候常在战壕里爬来爬去。福建一寸铁路没有,要先坐卡车出来,头上还戴着树枝编成的帽子以便隐蔽,飞机来了要赶紧躲。我一直生活在岛上从来没坐过汽车,所以一路上晕车晕得厉害,吐得一塌糊涂。出门时全部行李是一个小箱子和一把伞,吐得我最后把伞丢到哪里也不记得了。 在卡车上颠簸4天到了江西上饶,才看到火车。再坐一天火车,终于到了上海。那一年我只有12岁。 附中的生活一开始还是有点辛苦,那一年正好是苏联从莫斯科派专家来,苏联老师谢洛夫给我的功课非常难,他又是第一位派到中国的专家,每堂课都有很多人来观摩,所以每堂课都等于在表演一样,中学期间我跟过4位苏联专家。这几年的专业化训练,为我一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出国比赛之路 1958年,我第一次赴罗马尼亚参赛。由于刚更换老师,没足够时间准备,仓促上阵,没能拿到什么名次,但已经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走了第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