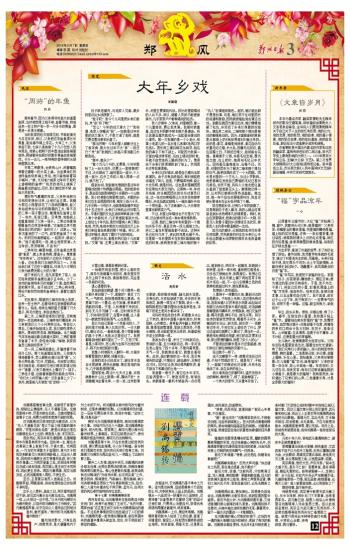|
||||
刘禹锡感慨世事沧桑,玄都观于挥毫作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之诗,将要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局。 对刘禹锡成见极深的武元衡览诗,以为 ‘无人不道看花回’是以下品之桃花暗讽朝中群贤,‘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讥讽自己是在刘禹锡走后才上位的,便急急入宫,求见宪宗。 观史而论,宪宗并非无道昏君,在唐朝皇帝中亦算是有所作为者。但终其一生,唯在永贞革新之事上耿耿于怀,不甚大度。究其因由,一乃当初与谋皇太子监国时,身为太子的宪宗亲眼看见父亲顺宗病卧榻上,完全任人摆布,因而极为痛恨王叔文等擅权乱政,将父亲用作傀儡;二乃宪宗登基之后,坊间流传其篡位及弑父弑叔流言,宪宗疑心是王叔文余党所构,因此更生忌讳。闻武元衡再奏,宪宗当即决定,必将刘禹锡等人再贬,不使生还。 翌日,正是复召官员入宫面圣之日。刘禹锡早起,明镜面前,拼命地想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出乎众人意料,面圣之日,宪宗皇帝却迟迟不到,却见武元衡从含元殿后走出。刘禹锡一惊,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以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武元衡提高声音,似乎在向众人宣布自己的绝对胜利,傲然宣布:“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 播州地处黔北,只有五百户,极度荒凉,是大唐疆域内下州之中的下州。将刘禹锡从朗州司马改为播州刺史,这是赤裸裸的贬黜。以刘禹锡所负时望,这一诏命可谓石破天惊,他泪水夺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柳宗元与刘禹锡感情最笃,颇知刘禹锡家中之事。刘母卢氏已近八十高龄,若刘禹锡果赴播州,则为死别。思索再三,柳宗元愿以柳州与播州相易,上奏朝廷。宪宗在裴度劝说下,使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柳宗元仍出刺柳州。 刘禹锡苦等十年,只在长安度过短短两月时间,便又要远赴海隅,令人好不唏嘘。新任刺史们虽留恋长安,但长安已无他们容身之地。刘禹锡又与柳宗元再出金光门,一同踏上了出刺州郡之路。 撇开二人友情,就诗中所见,刘禹锡的诗更多取法杜甫,也受白居易诗的影响,而柳诗兼取陶渊明与谢灵运。柳心性更激切孤直,故其诗既有近似陶诗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之作,更多的诗,情调凄怆,气氛幽冷,意向孤峭,缺少刘诗那种豪迈昂扬之气与清新朗丽之风,但刘、柳二人皆为中唐诗坛不同于韩、孟与元、白两大派的两位卓然独特的诗坛名家。 第十七章 刘禹锡踏潮迎波 两月奔波后,当刘禹锡来在桂阳县连州刺史府门时,他便不由想起了王叔文。“先历州郡,再掌台省”这正是王叔文当年为刘禹锡指出的道路。不过后来事情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刘禹锡凭着一腔热情纵横驰骋,却在帝国中央的曲直中撞得头破血流,现在,终于拐回到了原定的道路。 改授连州,于刘禹锡乃是不幸中之万幸。连州虽处岭南,但却是拥有十万百姓的上州,州刺史有从三品上的品级。刘禹锡从一六品司马一跃擢升为三品刺史,这意味着“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令已被打破,只要用心治理连州,获得优秀政绩而再擢近畿雄州,绝非难事。 刘禹锡甫一上任,便迎来海潮。刘禹锡领着府衙中人检视了公府仓廒,查看了河塘堤坝,督促公人将老弱妇孺转移到安全地带。防务皆备,再看天空,已是黑云涌动,疾风渐劲,四面隳突。 “使君,风雨将至,宜速回避!”衙役心中焦惧,不住催促。 “避?避往何处?”刘禹锡答非所问,不顾衙役劝阻,径自来到城楼上。豆大的雨点乘着咆哮的南风,狠命地砸向摇摇欲坠的城楼。刘禹锡扶住垛墙,艰难但坚定地对抗着愈加肆虐的狂风暴雨。 隆隆的滚雷穿透嘈杂的坠雨,耀眼的霹雳撕破黑暗的牢笼,在这场振奋心神的洗礼中,刘禹锡享受着狂风暴雨能奈我何的骄傲,任由风雨将身上仅剩的哀怨和晦气一扫而净。 衙役又来请道:“使君,此处危险,快随我去躲避吧!” 刘禹锡哪肯离去?反而大声问道:“如此雄壮之风雨,若在海边观看,岂不更妙?” 衙役大惊,回道:“这般风雨,只怕南海泛滥,冲入海塘,便成踏潮!某曾亲眼目睹,巨大的波浪铺天盖地冲上陆地,轰鸣之声震耳欲聋,横扫之地片瓦不存,若非逃避及时,必死无葬身之地!” 刘禹锡闻此言,更加神往。因思身负百姓命运,刘禹锡便听从衙役苦劝,回到坚固的屋中避雨。衙役升起火炉,为刘禹锡烘着衣裳,又讲述踏潮时排山倒海的非凡景象。刘禹锡按捺不住激动,从袖中抽出油纸包裹的毛笔,蘸着雨水,留下一篇淡淡的墨迹——《踏潮歌》。 在刘禹锡的精心尽职的安排下,这场四年一遇的强大海潮对连州的破坏,得到了有效的抵御。刘禹锡依朝廷惯例,先后作《连州刺史谢上表》《谢门下武相公启》和《谢中书张相公启》三篇文章。因这三篇文章分别上宪宗皇帝、武元衡和张弘靖,而此三人正是主导刘禹锡再逐远地的元凶罪魁。禹锡为文,实出无奈,文中聊作辩白,叨叙感激,并无真情。只在与裴度书信中,刘禹锡感激涕零,愿以死报。旬月之后,京城传来裴度回信,告知刘禹锡一桩惊世骇俗的大案。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遭重伤! 骄悍藩镇当街格杀宰辅、刺伤重臣,文武百官不但不以为弥天之耻辱,反而以藩镇凶悍为由,大放厥词,再谏宪宗罢兵停战,赦免吴元济之罪,并议罢裴度之官,以抚慰淄青、成德。 宪宗闻奏,勃然大怒,严厉斥责:“裴中丞大难不死,是天不亡朕!若罢其官,是奸谋得逞,朝廷无复纲纪。朕用裴爱卿一人,足破众贼!从今日起,长安内外务必严加搜捕歹徒,凡擒获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敢隐匿者,必夷灭三族!谁人敢复言姑息,必以附逆斩之!” 群臣惊惧,皆不敢忤逆。 待裴度伤愈,宪宗便令裴度补武元衡之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总领淮西军务。武元衡已逝,裴度入相后心中便有复召刘禹锡等人效命淮西之意。但以此试探圣意时,宪宗正为武元衡之死而伤怀,不欲使刘禹锡等回京而失与亡者君臣之谊。裴度只得将此中种种款曲付书禹锡,令其安心治郡,待有政绩,再行量移。 12 |
|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