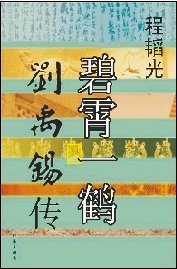|
||||
18 唐文宗在宫廷刀光剑影中被宦官扶上帝位,时时事事皆不离宦官掌控;朝中虽有裴度苦力支撑,却不及李宗闵之辈勾结宦官,熏天权势之下,裴度亦无可奈何。白居易回洛阳不久后,被征为秘书监而去长安,刘禹锡在洛阳困居半年,得一主客郎中分司东都的闲职,百无聊赖的生活,便在亲朋唱和与迎来送往之中继续蹉跎,这与他在二十三年沉沦生涯中日夜期盼的归乡生活有天壤之别。在恬静幽雅、孤独闲适的闲居中,刘禹锡师蜂自励,修德至勤,在表现“身闲志不闲”的高尚情操的同时,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其内心之不平,在于心系社稷。 又过一年,刘禹锡果然看到了重归大唐权力中枢的曙光。大和二年(828年)春,在宰相裴度、窦易直和淮南节度使段文昌的极力举荐下,刘禹锡调回京城,任主客郎中。 再度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刘禹锡心中横生孤傲。他笑了,他笑那么多灾多难的命运最终被他制服,踩在脚下。那些曾经对他恶语相加、造谣中伤之徒,还有几人能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主客郎中虽然官非枢要,但已有力地宣告,刘禹锡不屈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刘禹锡快马加鞭,赶赴京城。但他到达京城的第一站,既非投宿馆驿,亦非向郎署报到,却是去了玄都观。 元和十年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让刘禹锡复官梦碎,令他始终不能释怀。他曾无数次梦见玄都观中的桃花,他发誓有生之年必要再到玄都观,再写一首咏桃花之诗。 可是刘禹锡失望了。大和二年春天的玄都观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百亩桃花。昔年春游胜地,今日已成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仔细想来,也不奇怪。宪宗、穆宗两代皇帝皆因服食金丹而暴毙,玄都观受到牵连,道士们被驱遣一空。无人照料之下,桃花、道观何能独存? 失望过后,刘禹锡却又仰面大笑:这玄都观中的桃花,看来果真与他有缘!当年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引发轩然大波,而今不仅桃花都不见,连种桃树的道士也都没了踪影,岂不恰好暗喻了奸邪小人们失势灭亡的命运吗?满目的荒凉在刘禹锡眼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他无意于幸灾乐祸,但绝忍不住发出由衷的嘲讽: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再游玄都观》 然而,玄都观似乎是刘禹锡命中的煞地。命运便是如此荒唐,刘禹锡第二次在玄都观题诗,又令他的仕途遭遇了意外的挫折。刘禹锡刚刚望见的通往瀛洲之路,迅即被李宗闵之辈拦断了。《再游玄都观》一诗中透露出的桀骜之气和对新贵们的不屑之情,刺痛了李宗闵的神经。他指使言官上书弹劾,请托宦官屡进谗言,无所不用其极,硬是令裴度欲使刘禹锡知制诰的计划胎死腹中。 未能如愿知制诰,刘禹锡难免失落。裴度虽有同情之心,却无再擢之力,只能尽其心力,助刘禹锡在大和三年(829年)除礼部郎中,仍兼集贤殿学士,每日与古今典籍为伴,兼管判别从天下州道送来的各种祥瑞呈报。数年之中,刘禹锡在长安除编纂书册外,只能常随朝中阁老们饮宴游乐,做些应景唱和文章,虽然博得虚名无数,但他能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身体枯萎的声音,这象征着生命之火将要燃尽的声音不断敦促着他,一定还要为社稷做些实在的贡献。又经一年,刘禹锡将所编两千余册典籍进奉内廷后,终得外调之令,出为苏州刺史。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明水秀、风物清嘉的苏州是江南之冠,素来是唐代诗人的向往之地。加之,刘禹锡出生地离此不远,自幼在江南生活,任苏州刺史无疑使刘禹锡有归来之感。上任伊始,恰逢苏州水灾,刘禹锡为民请命,开仓赈饥,免赋减役,拯苏州百姓于水火。水灾过后,刘禹锡走入市井,探问农耕,教泽市民,安抚百姓。数月之后,苏州已复灾前繁盛之状。 浙西观察使王璠在苏州看到刘禹锡杰出的政绩后,在考课中将刘禹锡列为“政最”——这是和平时期大唐地方官员极少能得到的荣誉。朝廷特加褒奖,赐予刘禹锡紫袍、金鱼袋,以示荣宠。 获得紫金鱼袋的奖励,无疑是刘禹锡官场生涯中值得骄傲的篇章。刘禹锡明白,这也许就是他能在官场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但与朝廷所加紫金鱼袋相比,苏州百姓对刘禹锡的爱戴,才是令他最为欣慰的奖赏。大和八年(834年),刘禹锡在苏州百姓夹道相送的哭声中,在“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的不舍和惆怅中,调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御使后。此后,苏州百姓自发地建起“三贤祠”,以供奉曾为苏州做出巨大贡献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千年以降,香火不断。 第二十六章 存精神照耀后世 汝州离洛阳不远,刘禹锡任汝州刺史时,与同在洛阳的裴度和白居易往来唱和。刘禹锡悲哀地发现,裴度已经完全无意于朝政,他在洛阳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宅院,只愿一心安乐养老,白居易与裴度亦是同样打算。大和九年(835年),已经习惯了闲居生活的白居易以病为由,拒绝了授其同州刺史的任命。这顶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等使的乌纱帽,又落到了刘禹锡头上。“二华关渭水,三城朝合阳”的同州乃京畿门户,位置重要。只是同州已连遭四年大旱,刘禹锡上任后,除赈灾放粮外,就是引众赴山祈雨。祈雨途中,因年事渐高,不慎脚部受损,只好在府衙稍歇,并无多事。其本想静待时机,但一场惨烈的宫廷变故,彻底埋葬了刘禹锡再入朝堂的希望。 唐文宗并不是甘做傀儡的昏君。他先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使仇士良取代王守澄,并将王守澄赐死,然后又与自己提拔的心腹郑注、李训等人密谋,意图引凤翔官兵进京剿贼,引发“甘露之变”,可悲大业未成。再历此变,刘禹锡深感一己之力无法力挽狂澜,心生退意。在同州未满一年,刘禹锡即以足疾辞官,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甘露之变令唐文宗丧失了信心的支撑,仅两年便郁郁而终。面对宦官的暴戾,大唐几乎到了无人敢出来主持公道的地步。裴度去做了北都留守,不久告归,寿终正寝。牛僧孺来做了东都留守,日日宴乐,刘禹锡的生活便被牛僧孺、白居易等人的酒宴游乐所占据。 刘禹锡随着年事已高,时常被梦魇折磨,使他感知来日不多。刘禹锡拒绝家人为他请医诊治的建议,他对自己生命的掌握甚至超过任何神明。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就要走到终点了。当世能给他的,只有文坛上的些许微名,真正能读懂他的人,也许在未来。他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笔墨,诚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一生,好让后人能够从迷雾万重的史书中读到那个最真实的刘禹锡。 抱病之中,刘禹锡将生命最后的光辉,化入了《子刘子自传》中。作完自传后不久,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秋,刘禹锡溘然长逝于洛阳宅中,官终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后追赠兵部尚书,葬于祖坟荥阳檀山原。(完) 作家出版社出版 |
|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