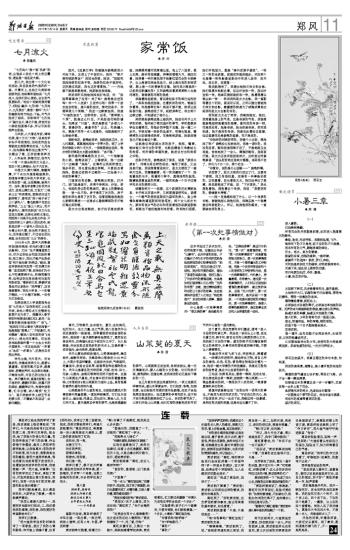|
||||
|
♣ 陈鲁民 “七月流火”是个很“坑爹”的词,让很多人在这个词上丢丑露怯,甚至是一些名家大腕。 前几天,我出席一个文化论坛活动,来自各地的代表济济一堂。开幕式上,当地文化局领导致辞欢迎,他热情洋溢地说:“七月流火,但我们的心更热,会议的气氛更热烈。”他这个词就明显用错了。《诗经·豳风·七月》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意即一颗叫“大火”的星渐向西方流动、下坠,天气开始凉了起来。该领导对“七月流火”望文生义,谬之千里,好在对这个典故知道得不多,所以引来的笑声也有限。 几年前,人大著名专家、博导纪某,是个文化“大咖”,说其没学识似乎有些冤枉,但他在欢迎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时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也错会了意,正好把意思弄反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作为一个有一大堆头衔的文化名人,在这个词上摔跟头,似不大应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厚,不下点功夫是难窥堂奥的。即便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也未免百密一疏,出现错漏,贻笑大方。当年,著名学者章士钊反对白话文,在报上撰文说,文言文“二桃杀三士”何其简洁,若换成白话文就啰唆了,要写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就禁不住发出笑声说,“三士”是三个武士,而不是读书人;继而讽刺说“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令章士钊大窘,他当然不是没文化,无非是记错了,不过他也因此受益,会永远记住“三士”的身份。 1998年6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著文《漫谈皇帝》。文曰:“生于高墙宫院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随后,著名学者钟叔河在同一栏目撰文纠错:“老百姓断了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笑话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看到钟文后,季羡林诚恳地对记者表示:“我弄错了,应该是晋惠帝。”两位大学者,一个纠错不嘲讽,一个认错不辩解,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如果说连文人学者都难免会在“七月流火”这样的词汇上出现失误,其他人等犯点文史错误也就更不足为奇了。美籍华人歌手李玟听到歌曲《满江红》,就问:“这首歌的歌词是谁写的?”“岳飞。”“那我可不可以请岳飞帮我写歌?”她是典型“香蕉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错把八百年前的岳飞当成今人,倒也无可厚非。可当我在电视剧里听着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演员,一本正经地把“一抔黄土”念成“一杯黄土”,还是没忍住笑出声来。 学无止境,天外有天。无论是研究、传播或卖弄文化,都要认真谨慎。即便有真才实学,满腹经纶,若需发声时,也应做足准备,不能想当然,对自己的记性太自信。弄不懂的词,查查《辞海》,念不准的字,翻翻《字典》,把握不好的典故,翻翻常识书,免得张冠李戴,忙中出错,被人嘲笑“没文化”。再不然就学学上综艺节目的蔡少芬,“不懂就不乱说话”,这就叫藏拙。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