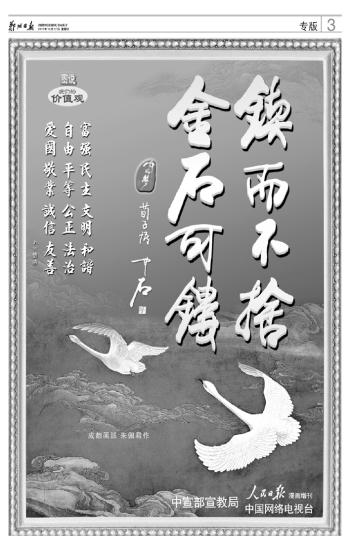
|
| 第03版:文摘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
拷问灵魂的翻译家 武 杰 2017年10月6日,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高莽的翻译生命期长达70年,他将一生都献给了心爱的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 1943年,17岁的高莽翻译的第一篇译作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但是在他看来,真正开始从事翻译其实是1948年翻译剧本《保尔·柯察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高莽看到了邦达连科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出于喜爱,高莽将它翻译成中文,印成书后还被搬上舞台,当时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保尔·柯察金。 高莽生前常常谈起保尔·柯察金对他的影响,那些名言让年轻的高莽激动不已。当时高莽其实正面临着人生的难题。“二战”时,哈尔滨被日军侵占,在哈尔滨长大的高莽,并不喜欢顶着翻译的名字,因为大家都骂翻译是“狗腿子”“走狗”。 1949年,他遇见了最早译介普希金与高尔基的翻译家戈宝权,戈宝权一句“重要的是翻译什么作品和为什么人翻译”点醒了迷茫许久的高莽,“我翻的是大家需要的东西,我要翻译革命的作品,是给老百姓看的”。 此后高莽便有了“乌兰汉”这个笔名,即“红色的中国人”。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深明翻译之苦之难后,他将“汉”字改为流汗的“汗”。翻译是要流汗的,绝非轻易之举。可许多人不知道,高莽并没有上过大学。 高莽说自己是在为茅盾、老舍、巴金等知名的大作家做口译时,上了“大学”,“那时候我每天都可以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谈话,给他们做翻译,有不懂的时候就问他们。我的这点知识、这点本领就是这些老先生们在工作中教会我的”。 高莽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是随着人生的阅历不断变化的,最能说明的是晚年翻译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2013年,高莽凭借译作《安魂曲》,获得“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对此,他说:“我虽然做的只是翻译,但拷问的是自己的灵魂。” 摘自《法制周末》 杨辛:不给生命设终点 张 鹏 研究了一辈子“美学”,却偏居北大老旧的红楼,爬上逼仄狭窄的水泥楼梯,敲响一扇锈迹斑驳的防盗门,开门的是一位满面笑容的老先生,他就是美学专著《美学原理》作者、95岁的北大“长寿哲人”杨辛教授。 乐观豁达的杨辛也经历过退休后的一蹶不振,身心憔悴,“我刚退休时不太适应,产生过悲观情绪,觉得生命就是一条直线,从起点到终点,白驹过隙,匆匆过客,虽然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情,可心里总有一个阴影,觉得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如何摆脱这种悲观情绪呢?杨辛说是爬泰山的过程中开悟的。 1979年,57岁的杨辛赴济南参加美学研讨会,会后与友人结伴登泰山。从望岳到登临,杨辛终于领略了李白的“目尽长空闲”和杜甫的“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泰山仿佛一位静候已久的知己和导师,瞬间应和了杨辛全部的人生理想与美学理念。打动他的,不只泰山美景,还有泰山默默记录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 回京后,杨辛意犹未尽,感觉泰山仿佛在远远凝视着他,期待着他,要通过他讲述什么,从此对泰山成痴成迷。退休后,杨辛一次次地回到泰山。几十年间,他几乎踏遍泰山群峰,博览泰山历史。每次登临之后,杨辛都要挥毫赋诗,以言心志,至今已创作30余首诗歌。 在老人巨大的书桌上,放着他做的一首小诗:“人生七十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最后一句是我要表达的对生死的哲学思考,到了期颐百岁之年,四季看似已经走到头,可是迎来的是春回大地,这就是生命的循环。我现在不认为生命是一条直线了,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圆,圆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人的一生有限,个体生命结束了,融入宇宙的大生命中去,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寿,人从自然中来,回到自然中去。”不给生命设终点,每一天都会过得愉快而有意义,杨辛认为,这就是生命的自由。 摘自《北京青年报》 |
| 下一篇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