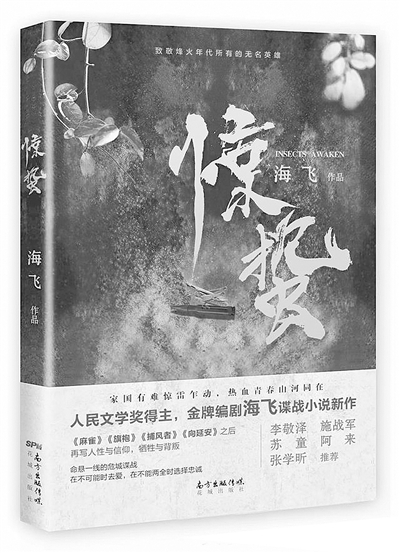|
| 第07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陈山笑了。他对张离认真地说,当汉奸的是不是都有一个请当红婊子跳舞的梦想? 张离并不喜欢陈山用这种轻佻的语气来评价一个女人,她的脸上没有笑容。她说,你的骨头有点儿轻! 但是陈山仍然果断地拉着张离迎向了唐曼晴,这时候唐曼晴正带着陈河和几名日本人谈得正欢,唐曼晴的日语讲得比日本人还好。她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看到了阴着一张脸的陈山和陈山身边不知所措的张离。陈山说,真巧,世界那么小,小到只有米高梅那么大。 张离的目光落在了陈河的身上,在巨大的震惊中她发现这个和日本人聊得正欢的男人,就是她牺牲在围剿战场上的未婚夫钱时英。张离努力地让自己脸上的表情平静下来,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她紧紧地挽住了陈山的手。钱时英却像根本不认识她似的,彬彬有礼地向她弯了弯腰,这让张离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而荒木惟在整个舞会中,安静得像一个哑巴。他坐在东南角的角落里,抽那种叫蒙特克里斯托的雪茄。他一直都被浓烈的烟雾笼罩着,远远看去,几乎看不清他的脸。除了不时地举杯向麻田长官致敬以外,绝大部分时间他选择了沉默。 那天陈山从陈河,也就是现在的大药材商人钱时英手里半请半抢了唐曼晴。唐曼晴从钱时英的目光中,读懂了钱时英的意思。她没有拒绝陈山,和陈山在舞池里转着圈。陈山的思绪也在转着圈,哥哥为什么被日本人叫作钱时英?他怎么和唐曼晴还有日本人走得那么近?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音乐停止的时候,唐曼晴说,你跳得很好。 唐曼晴又说,比时英好多了,但是你的舞练了没多久。不会超过半年。 陈山心中暗暗叫好,说你的眼睛很毒。 唐曼晴笑了,说,我还能看到你骨头里面的自卑。你不要对时英不服气。你和他没得比。 那天,陈山还是在张离极力要稳住的舞步中,捕捉到了她稍纵即逝的一丝慌乱。张离把头靠在陈山的肩膀上,微笑着咽下了眼眶里的那点激动。陈山轻拍张离的后脑勺,他感受到了张离身体的微颤。而其实在刚见到陈河时,张离紧紧挽住了陈山的手臂。她的微颤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陈山。陈山什么也没有说,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名特工了。 荒木惟就坐在一片灯光暗淡的角落里,雪茄抽动时一闪一闪猩红而热烈的火光会在某一个瞬间照亮他冷峻的脸庞。舞池中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别想逃开他的眼睛。他仔细回想着舞会上众人的反应,直觉告诉他,今天的舞会暗流涌动。他决定要试探一下陈山。而张离这个跟着陈山投奔上海的情妇,也令他暗中生疑。 舞会结束的时候,唐曼晴婉拒了麻田长官的邀请,在霞飞路培恩公寓自己家中给钱时英拔火罐。唐曼晴出奇的安静,她不作声,她不晓得此时的钱时英正无数遍的回想着刚刚相见的张离。 是小赤佬让你生气了?唐曼晴终于忍不住了,一边起罐一边说。 他不是小赤佬。我不许你这样叫他。钱时英说,他很聪明的,我们三兄妹中,他顶聪明。 唐曼晴把一块热毛巾搭在了钱时英的后背,说,对不起。 唐曼晴最后说,你血瘀很厉害。全紫了。 趴在牛皮沙发上的钱时英很久都不作声,他把头埋在沙发中,仿佛陷入了很深的回忆。后来他起身,穿上了衬衣,然后坐在沙发上。半晌他才说,我爹对他并不好。 那天晚上,唐曼晴说,那么晚了,你留下吧。 钱时英还是没有说话。唐曼晴一会儿又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几口,又在烟缸里揿灭了,说了两个字,你走! 贰拾 第二天早上,陈山在梅机关见到了荒木惟,他正在弹琴。陈山在那张墨绿色的西洋皮靠椅上坐下来,他欣赏着荒木惟的琴声。荒木惟没有回头,他只是随意地问了一些问题。在荒木惟不紧不慢的提问中,一阵困意袭来,陈山渐渐失去了意识。陈山不知道荒木惟想通过催眠的方式探探他的虚实。一个遥远的声音,好像是从云层里掉下来的,在和他不停地说着话。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松了,整个人就像在梦境中,头也越来越沉,仿佛随时都可能掉落到地上。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能睡着。他的手指头摸索着,终于摸到了一排加固皮靠椅的圆帽钉。 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在不停地问自己,你在重庆做了什么? 在荒木惟的问话中,陈山看到了辽阔的画面在自己的脑海里慢慢拉开了沉重的幕布。一道白光亮起,他看到了自己正在军统第二处机要室用千田英子给他拓的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了那张高射炮部队炮群布防图。他的脸上浮起了笑容,觉得他和妹妹陈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这时候他的脑袋被一把枪顶住,他无奈地举起了双手。一只手伸过来,把他手中的布防图取走。然后费正鹏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只是守株待兔。 费正鹏说,你第一次在我面前抽烟被呛着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装的。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国。 费正鹏又说,这一着,就叫诱杀。 陈山脑海里浮动着的画面,像河里的水草在太阳光的映照下不停地飘摇着。他张了张嘴,发出了啊的声音。这时候荒木惟已经离开了钢琴,他正站在陈山的面前,双手撑在椅架上,微笑地近距离看着他,如同一位慈爱的兄长。荒木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刚才想到什么了?你说。 陈山觉得自己很心慌,于是他命令自己,把指甲硬生生地往圆帽钉里剥。就在他快完全被催眠的时候,剧烈的疼痛从手指头开始向大脑传达。他像一个在水中快被淹死的人,努力地想要睁开眼,终于他被疼痛叫醒了。他睁开眼,眼神迷离地望着在他面前晃动的那个人影,说,我刚才怎么睡着了。 那天中午,在梅花堂院子里的阳光底下,面对陈山再次提出要见妹妹陈夏的要求,荒木惟淡淡地说,不要急。离你们相见,还有3次电话的距离。到时候我会还你一个天使一样的妹妹。那天荒木惟开始穿夏装,他仿佛并不怕倒春寒,所以他穿的是一件雪白的衬衣。这样的白,晃了陈山的眼。后来陈山走出了荒木惟的办公室,缓慢地走在了走廊上,像一个生病的人。 在陈山的脚步声里,重庆的细节重又浮了起来。费正鹏收起了顶在陈山脑袋上的枪,在与陈山的一次长谈之后,费正鹏和处长关永山请示了军统的最高机构甲室。 15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