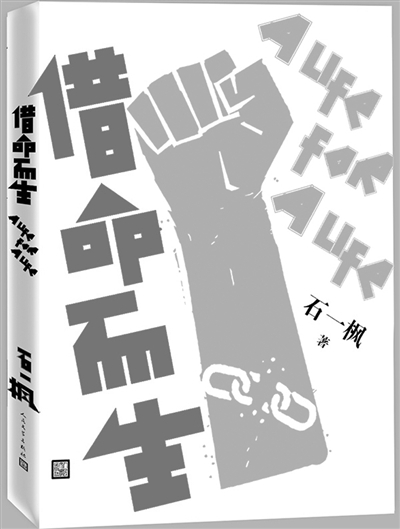|
||||
出了盥洗室,“杆儿犯”仍想含混其词,杜湘东一句话就让他“秃噜”了:“要不你去单间,请吴管教照顾你几天?”老吴有着许多花样百出的折腾犯人的办法,这是出了名的。而据“杆儿犯”交代,斗殴的起因也很简单。新进来的人第一顿饭往往是吃不上的,姚斌彬分在十七监,恰好和郑三闯同屋,所以昨晚的窝头刚发下来,他那份儿只好被迫上供。到了今天早晨,郑三闯又盯上了姚斌彬手上的纱布——他前几天刚上完镣,脚跟子磨破了,还化了脓,正缺一块裹脚布。但这次的要求却碰了壁。姚斌彬还没说什么,隔壁十八监的许文革先不干了,吵吵着说不能欺人太甚。 郑三闯就乐了,道,不服?不服你“翻板儿”呀。 监舍里的大通铺就是一块木板,故而犯人们的黑话都与“板儿”有关。每天面壁反省叫“坐板儿”,新人进来挨一顿杀威棒叫“走板儿”,有更蛮横的人物把老牢头取而代之就叫“翻板儿”。而许文革八成是没听懂,又见水池上架着一张摆放牙缸的木板,居然真把它抠起来往上一掀,溅了郑三闯一身牙膏沫子,还吼道,翻就翻,翻了你就别烦我们。 此言一出,问题就严重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里面,统治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铁与血的斗争。郑三闯就让动手。而许文革还真有两下子,上来就把郑三闯的头号打手,一个络腮胡子的东北人按在地上了。随后便有更多的人像疯狗似的扑上去,除了打许文革,还打姚斌彬。为了护着姚斌彬,许文革就落了下风,一边挨揍一边说,打我得了,别打他。郑三闯又乐了,有条件地接受了许文革的要求:仗义是吧?碰上仗义的人,得先验验是真仗义还是假仗义;那就先打你,什么时候你抗不住了,再让他替换你。 杜湘东明白,郑三闯的本意并非是要打出个你死我活,无非是想把许文革收服了罢了。只要说声“服了”,顶多再按北京街面儿上的规矩叫声“爷”,也许从此还能混上一把交椅。混混儿也有混混儿的爱才之心。没想到许文革愣是没服,用身体罩着姚斌彬,咬牙挺了许久。就有人嘀咕,看来这孙子是真仗义。这反而让郑三闯下不来台了,他也不能停,一停就是他“服了”,于是让手下发狠再打,而且专照要命的地方打。又有人劝,说再打就出事儿了,郑三闯却被激出了横劲儿,说有事儿我担着,大不了一年劳教变十年大牢。就这样,打与被打的拉锯战持续到了杜湘东到来。 “杆儿犯”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人,连吭也没吭一声。” 这时老吴总算歇够了,慢悠悠地踱了回来。杜湘东斜了一眼没说什么,让他先带犯人回监舍,自己则去通知狱医。许文革挨了几百记拳脚都有神智,突然松下来,反而没走两步就晕过去了,头磕在水池上,又冒了不少血,只能用担架抬往医务室。料理了伤员,杜湘东这才腾出手来处理后续事宜。他到十七监宣布,郑三闯从今天开始重新上镣,参与打人的帮凶劳动量加倍,持续一个星期,完成之后才能吃饭。然后他指指郑三闯位于靠门处的那个专享铺位,又指指姚斌彬:“他这儿给你睡,他回头睡尿桶边儿上去。” 郑三闯眼里凶光一闪。被剥夺了最宽敞的“头板儿”,这相当于失去了牢头地位的象征。而杜湘东特地又“照”了他几秒钟,表示此意已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接着招呼姚斌彬:“你过来。” 那孩子小步往前挪了几尺,脸仍煞白,眼瞅着又要哭了。他的模样再次让杜湘东烦躁起来,训斥道:“不准叫妈,叫妈就把你嘴铐上。” 又说:“你那同犯是为你挨的揍,你就是不能给他帮忙,也别给他丢脸。” 姚斌彬上牙咬着下嘴唇,惨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睫毛下涌了出来。 最后,杜湘东扫视监舍里的所有人:“他脸上有几道伤,我可都记着呢。从今天起只能少不能多,多一道,我唯你们是问。” 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看守所的监舍虽然封闭独立,但自有一套传播小道消息的途径,于是接连几天放风的时候,犯人们都会对他侧目而视,还有偷偷上去“盘道儿”的。杜湘东本来担心郑三闯会报复,但事实证明他多虑了。那个戴着脚镣、屁股后面拖着俩大铁球的老炮儿虽然看见姚斌彬和许文革就阴着脸,但当手下的兄弟又想去找俩人麻烦,却被他一个眼神就瞪了回去。郑三闯还下令,以后谁也不准再抢姚斌彬的饭。这么做当然不是要给杜湘东面子,而是因为老炮儿行事自有老炮儿的原则。对于够硬气、够仗义的人物,就算是仇家,他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而俩犯人再次让杜湘东另眼相看,是在劳动的过程中。 劳动就是制作象棋子和冰棍棍儿。对于所里,这算创收途径,对于犯人,则是必不可少的改造任务。除了死刑犯和卧病在床的,其他人无论刑期长短、年纪大小,概莫能免。在劳动时,犯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具体地说是分成体力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和半个艺术工作者:大多数人发张砂纸,打磨上游加工出来的半成品,这是最费工也最枯燥的流程;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犯人则被委以操作车床和冲切机的重任;还有一些会刻图章的,那几乎是所里的宝贝,冲压上字的象棋子都得靠他们进一步修饰加工,“车马炮”才能成为整齐的篆文。姚斌彬和许文革是工厂出来的,自然被指定在了车床旁边,但因为是同案犯,俩人不能搭班,而且还被远远地隔开。许文革果然底子好,不出两天,车出来的象棋子的合格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了,而姚斌彬的纱布虽然摘了,右手仍不灵便,操纵不动机床,所以干了两天又被扒拉回了打磨组,用胳膊肘夹着棋子干活儿。 这天正在看着犯人赶一批订货,就听见铿啷一响,一枚残缺不全的象棋子飞了过来,恰好落到杜湘东倒放在窗台上的大檐帽里。他正靠墙想心事,蓦地一惊,还以为又有人打架了,或者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破坏生产工具来反抗剥削的迹象。但抬头一看,闷热的车间秩序如常,只有最靠把角的一台车床停了下来。负责操作它的那个交通肇事犯愣乎乎地站在一旁,显然也被吓了一跳。 杜湘东吹了声哨子,提醒把守在车间门口的同事注意警戒,又捅了捅歪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吴,招呼他一起过去看看。来到车床旁问怎么回事儿,交通肇事犯也不知道,表情像当初看着自行车道上的尸体时一样茫然。杜湘东又转了转车床上的摇杆,一动不动,不知是哪儿卡住了。正在这时,他的脚边却多了一人,姚斌彬不知何时从工位上闪了过来,蹲在地上,伸着脖子打量着这台车床的底部。 6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