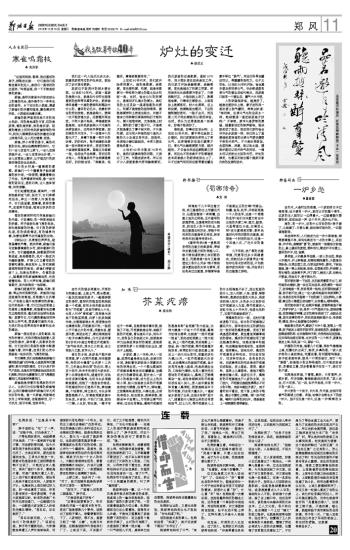|
||||
|
♣ 赵成义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太多太多,就拿我家使用过的炉灶来说,就经历了多次革命更新。 老家位于老郑州的城乡接合部。20世纪50年代,家里一直烧的是柴火灶,就是如今农村也很难看到的那种带风箱的炉灶。厨房里常年堆着一大堆的劈柴和树棍杂木什么的。童年的记忆中,我最初学会的劳动技能,就是烧柴火。劈柴一次不能放得太多,还要错开架空放,不然火烧不起来,弄得满厨房都是烟。当年我家烧柴火不光是用来做饭烧水,还用来冬季取暖。那时候的冬天可冷,下一场雪半个月都化不了,房檐下挂着一两尺长的冰凌。奶奶怕冷,每天临睡前总要烧一些木柴到半炭状,放进瓦制的火盆端到屋里驱寒。屋里立马温暖一些,但却会产生烟雾,有时还有点呛人。而每逢我对产生烟雾提意见时,奶奶就会说:“烟暖房,屁暖床,熏得被窝暖洋洋。” 上世纪50年代末,我们家开始使用煤火,烧的是散煤。烧散煤,首先要和煤。和煤,就是将散煤与一种俗称为煤土的黏土加水和到一起。当时,省会公认的好煤土,是南郊齐礼阎乡的煤土。黑红色的土还夹杂一道道很黏的白筋儿。和煤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要根据煤质和土质适当配比,并要不惜体力用铁锹反复捣持拍打才能和匀。煤火很难伺候,尤其是晚上封火。煤和软了硬了都不行,不是熄灭就是着乏了撑不到天明。不只是和煤,还与用火杵捅的那个通风火眼的大小及歪正有关系。那些年,母亲很少睡过囫囵觉,半夜三更总要起来看火。 上世纪60年中期至70年代初,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出了工伤,长期在家休息。所以当不少人家更新换代使用蜂窝煤时,我们家烧的还是散煤。直到1975年,我从部队退伍回来参加工作,我们家才开始烧蜂窝煤。烧蜂窝煤,首先是减去了和煤之劳累。使用起来也比烧散煤方便多了,只要把眼对正,火很快就上来了。换煤很省事,只需将乏煤取出,上面再加上新煤即可。封火也简单,压上两块煤,把煤眼适当错开,下边的插板插好即可。一般不会灭,而且第二天不用加煤就可以做完早饭。当时,我认为这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好得不能再好了。 谁知道,好事还在后头呢!上世纪80年代初,妻子单位给职工办福利,我们家竟率先使用上了液化气。这使得街坊邻居们羡慕不已。液化气比蜂窝煤更方便,随开随用。不仅省去来回运煤搬煤之劳累,而且也不用将黑乎乎的煤堆放在本来就狭小的厨房或阳台上了。只不过是气用完后还要带着空罐去妻子单位“换气”。用自行车带空罐还可以,带重罐有些吃力,也不太安全。20世纪90年代开始,省会基本普及使用液化气,许多街道都有液化气的营业店或代销点。我家路口就有一个营业店,灌气十分方便。 人的欲望很奇怪,越是好了,越是往更好处上想。妻子在和我一起往楼上抬气罐时,常常企盼道:“啥时候,这液化气也和自来水一样,能顺管道一直送到家里才好呢!”不承想,原本只是梦想的愿望,随着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现在我们家和省会许许多多家庭一样,早已用上了直接通到厨房里的比液化气更快捷更干净的天然气。不只是炒菜做饭,包括洗澡、采暖,配以热水器、壁挂炉都可以用天然气来完成。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炉灶的演变,也着实反映出整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 |
|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