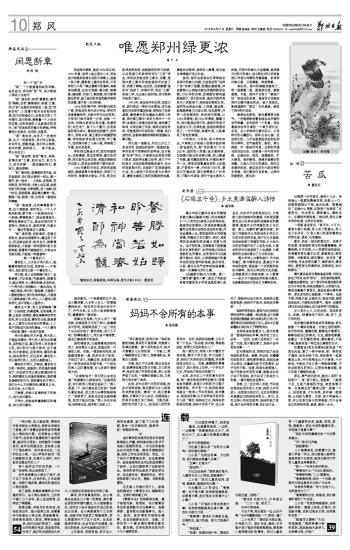
|
| 第10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
♣ 卞 卡 我在郑州栽树,是在1956年以后。1953年夏,我考入省立郑州二中,校址在大同路东段南北向的弓背街上。那是一条小街,整条街上基本没有树,只有学校门口有一棵还算高大的榆树。周围其他街道,比如大同路、德化街、钱塘路、操场街、乔家门、解放路、西大街等都没有树,除了破旧的民居和略作修饰的店铺,看不到一点点的绿。 1954年秋季开学,学校搬迁到京广路,即现在的郑州四中校址。学校对面是蜜蜂张村,印象中村中也没有树,只有校门斜对面有一片树,却是一个坟场。校园内原来也有坟墓,因盖学校,坟迁走了,留下几个墓穴,还有残留的棺木碎片,看到那坟那墓穴,因年龄小,我有点怕,晚上曾多次被噩梦惊醒。学校组织学生美化校园,平了墓穴,在校园内修了几条小路,两侧栽了冬青,但没有栽树。 学校西边是金水河,那时河里有水,还很清澈,岸边有柳树,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河边洗衣服,将湿衣晾晒在河边草上,然后坐在柳树下聊天纳凉。 1956年夏初中毕业,按我的家庭境况,继续读高中困难很多,我报了三所技校,想着早点就业。不料,班主任老师突然找我,说根据我的学习成绩,以及连续三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学校决定保送我上高中,说着,把郑州第三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我做了解释,但无用,无奈拿着“通知书”回家了。秋季开学,我去“三高”报到入学,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与栽树开始有了缘分。 1954年,省会由开封迁郑,在那之前,原行政区一带多为庄稼地,因为省直机关多被安置在那里,便规划了多条道路,最宽最长的当属金水路和人民路。郑州第三高中(后改为郑州十一中学)坐落在人民路中段东侧,虽然铺了柏油,中间还修了花池,路两边却没有树。可能是郑州市政的统一部署,我们进校后,在新辟道路两侧栽树便提到议事日程。 我们那一届新生,约近三分之二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一般都较差。学校设有不同等级的助学金,但只能是“助学”而已,于是便主动同有关部门联系,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周六下午和周日,去饭店择菜刷碗抹桌子,去木材场挑拣木料,去面粉厂扛面袋装车外运,去二里岗火车站仓库为水果分类,暑假去建筑工地和泥搬砖挖地基,寒假则去栽树。虽然收入微薄,却也给日常零星开支以补贴。 那时,省市当政者似已考虑到未来郑州的绿化问题,已在现在的“经纬广场”专辟了苗圃,培植法国梧桐,并在紫荆山公园刨去野生洋槐树换成法桐,1956年的时候,法桐都长得鸡蛋般粗细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市园林局技术人员指导下,将那些法桐挖出来,装汽车运到金水路、人民路、建设路、陇海路铁路文化宫以西、经五路等,并按一定距离放好,然后进行栽植。从1956年寒假,到1958年寒假,整整三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开学前才回家住几天。庆幸的是,那些法桐都成活了,一天天变粗,枝繁叶茂,几条路有了浓浓的绿荫。 十年树木。几年后,我从学校毕业,不承想又分配到人民路中段东侧一家省直机关,离“我的高中”不足200米。那时的人民路、金水路两侧,已被高大粗壮的法桐占据,树上搭满了鸟窝,夏天藏在枝杈间,叶落后黑乎乎一片,常有成群鹭鸶在树的上空盘旋,不啻郑州一景。大约在1965年,著名文艺理论家、散文家萧殷从广州来郑,下榻中州宾馆,穿行于金水路和人民路,对郑州的绿化大发感慨,遂写散文《郑州的绿》,发《奔流》和《羊城晚报》。作者以写意和抒情笔触,极写郑州绿之美,文笔清新,深受赞誉。 再往后,郑州的绿越来越浓了,树一茬接着一茬,都根深叶茂,郁郁葱葱。于是,郑州不仅有了“绿城广场”响当当的名谓,甚至可以说绿在郑州已铺天盖地而来,除了老城区,新辟道路和“新区”处处是绿,绿成了郑州的代名词。 绿是生命原色,象征着青春与朝气,一定程度影响着地域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多年前的一个初夏,我应邀参加吉林长春的一个散文研讨会,会后,主人安排我们游长白山,从吉林市的山麓进山,驱车20多公里,迎送我们的,几乎全是原始状态的松树和白桦林,空气是香的,甜的,爽心爽肺。对一般城市而言,这样的环境当然无法比拟,但绿是一叶叶张开的肺,这是共识。因而,培植绿色,扩大绿色,保护绿色,既是环保意识的觉醒,又是人们行为的准则。郑州正在阔步前进,绿正在成为大家共赏的主色调,我们要且行且珍惜,让郑州的绿更浓,更出彩! |
| 下一篇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