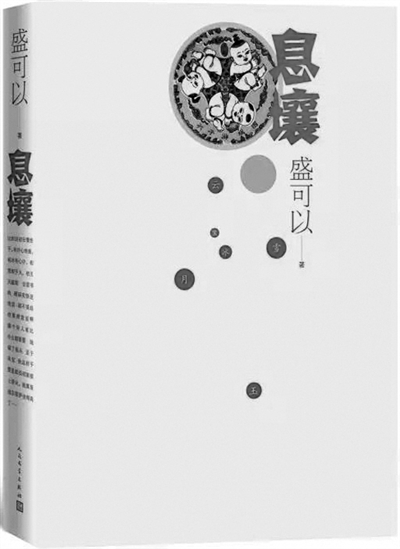|
||||
有人发现她夜里从坟地的方向回来,如果不是想碰鬼,没有人会在夜里去那种地方。她似乎见过初安运的鬼魂,但凡夜里这么走一遭,白天那双绵羊般温和的眼睛便会更显安宁。 吴爱香裹上头巾后好像变了一个人。有些妇女开始学她的样子,也把头发裹起来,没多久村里的妇女头上都是花红柳绿的。各人裹发的样式不同,有的简单围在头顶,露出半截头发;有的裹好头特意留下一截头巾随风飘摆。人们进一步发现头巾的好处,炒菜隔油烟,干活防尘灰,热起来还可以挡太阳、抹汗,谁家建新房上房梁朝地下扔糖果饼干,扯开头巾比谁都接得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妇女裹头巾的现象,是不是吴爱香发明的已无从考究,但她的确是村里第一个戴头巾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束后,新成长的乡村妇女对头巾不屑一顾,她们明白头发是女人的第二张脸,经常结伴去城里洗发烫发做发型,买同款式的衣服穿,私下聊些床上的事情和女人的秘密。老妇人们也早已陆续解下头巾,有老骨头发硬抬手费劲的缘故,也有时代风气变化的原因,总之,裹头巾是一场自觉自愿自我束缚与自我解放的自娱自乐——她们自然不会同意赋予这一行为更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或许可以理解为乡村妇女趋同的跟风打扮,是她们保求安全不被指指点点的心理表现。即便到今天仍然如此,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要相同,甚至房屋建筑,也是长得一模一样。 吴爱香是村里最后一个摘下头巾的女人。当她结束喃喃自语的晚年,永远地闭上嘴巴,人们第一次看见她稀稀落落全白的头发,脑海里还停留在她满头黑发的样子,诧异于她的头发仿佛是一夜间白掉的。 这已是2016年的事情。 她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如果允许她从棺材里爬起来作一次发言,让她谈一谈自己这辈子的感受,她一定会说如果没有肉体, 活着是一件十分轻松的差事——她不知道说,情欲这种词,情欲是文化人说的,村里人通常说发骚 。这样的语言过于粗俗,她也说不出口,她只知道说肉体,这个词就像一个人穿得老老实实,没有可以让人指手画脚的地方。但即便这个世界跟她没关系了,她也难以启齿,在无数个夜晚,她体内的渴望与冲动。她认为她自己并没有情欲,是她的肉体在提醒她、催促她,好像她欠它的,因为它的生活规律被破坏了,而她无视于它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弥补措施。 上环时医生的判断是对的,那些年与初安运的性事的确相当频繁,天昏地暗,甚至让她觉得堕落羞愧,而她的肉体每每欢欣愉悦。她为自己的虚伪羞愧——这些她也不好意思讲,尤其是在那么多生前并没有关心过她的生活的亲戚面前,当他们睁大窥视的眼睛,打定主意要装点东西在回家的路上咀嚼时,她要做的便是如何更好地捂住自己的隐私,绝不让他们得逞。她会微笑着像给自己写墓志铭一样告诉他们。 我的运气很好,嫁了一个好男人。虽然他死得太早,但我们有六个听话的崽女,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有个好干娘当家做主。冇她我们都活不下来。 她更不会打开内心封锁了几十年的秘密,破坏人们心目中那个纯洁的寡妇形象。 守寡第八年的秋天,她干了一件连她自己都没料到的事。那一年干旱,少雨虫多,蔬菜被啃得只剩茎叶,稻田里蚁虫一团一团。她有几回进城买杀虫剂。每次经过街角,她总能碰到坐在光线幽暗的杂货铺里的男人发亮的目光,这目光渗进她空空荡荡的心里,照见一个没有家具的房间和苍白的墙壁。整整八年她没有这样直接地对碰男人的眼神,连近在咫尺的男人气味都没闻到过。 杂货铺里那双在幽暗中发亮的眼睛带着善意和想跟她搭讪的欲望。有一次,他盯着街面,看见她便站了起来,仿佛就要开口打招呼,她赶紧埋头甩下他,脑海里却印着他高大结实的身板,约莫三十七八岁。她嗅到他公牛般的气息,这气息像百爪鱼一样追上来,缠住了她。逃离这条街,她感到恐惧仍然紧攥她的心并没松开,同时意识到身体某处湿漉漉的,羞耻感让她呼吸更加困难。 她有一阵没进城买东西,或者有意避开那条街,然而只要想到他,她的身体就湿漉漉的,饥饿与疲惫。 她是在干旱接近尾声的时候去的杂货铺。 那天她裹了一条草绿色的头巾,或许是因为秋风,她裹头巾的方法有所改变,遮住了耳朵和两侧脸颊,在下巴处绕到后脖子打了一个结。她的首要任务是给戚念慈买风湿膏药,后者的小脚预报天气要变,即将转冷下雨。她也攒了很多必买品,让婆婆相信已经到了非买不可的时季,否则萝卜白菜就要错过下种的机会,总之,她出门的理由无懈可击。 这一天她走得比任何一次都快,好像怕什么东西凉了似的。 她去得太早,杂货铺那排竖木板牢牢地挡住店门。去买别的东西时她紧张得要命,不是算错数,就是付了钱忘了拿货。卖菜籽的老板说:“你这个堂客怎么丢了魂魄似的。”她才知道自己的表现有多么可笑。这使她加快了要做那件事情的速度,仿佛怕自己变卦。 她返回杂货铺,木板还是一块块并排站着,牢牢地守卫后面的领地。她嘭嘭捶响了木板,敲得又急又响,好像发生了火警。她那时候其实满脑子空白,只是机械地完成大脑的旨意把门敲开。里面男人问:“谁?” 她回答:“我。” 好像两个熟人事先约好的幽会。一扇小门打开了,她甚至没看那男人惊喜的面孔,只顾闪身进去,随手关上了小门。 直到她拾掇好自己离开杂货铺,两个人都没说一句话。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那天的街上非常清静,她是后来被脑海里自己捶门的声音吓得胸口怦怦直跳。等到快走到村子里的时候,她仍未平静,一种崭新的、异常的感觉笼罩着她。 这下我的肉体可以安静下来了。这应该够我挺几年的,她手里牢牢地攥着该买的东西。 她有一个月没在街上露面,尽量打发孩子去买东买西。 有一天,那个男人找到村子里来了。她正在厨房做饭,从后窗看见他在长堤上缓慢地行走观察,两只手揣在裤兜里,有时看看天,在一棵树下坐上片刻。她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必定问过很多人,才能知道她住在这一带。她惊得脸上肌肉都颤了起来,那个早上捶响杂货铺的女人只活了片刻早就化成了青烟,她现在是一个纯洁的寡妇。然后她心里也有一丁点被人惦记的欢欣。他来找我,想必也一直在等我。 12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