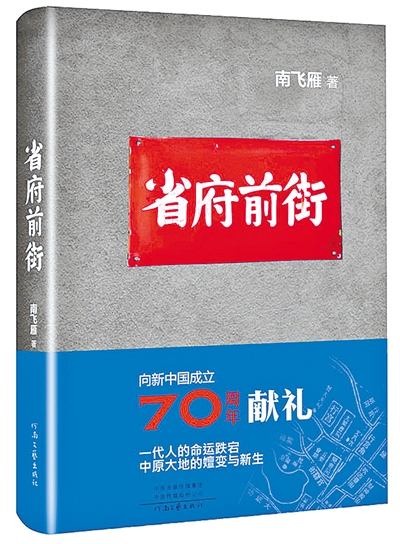|
||||
徵茹吃惊道:“动手?” 这时已经到了三义家门口,圣衍沉着脸,再不言语。父子下了车,把车和牲口赶进院子。老三义早听见动静,拖着残腿迎出来,见是圣衍爷俩,也是一脸的惊愕。圣衍扑通跪下,道:“给姥爷请安!” 老三义七十多岁了,那年中牟大疫,全家人死得只剩他一人,若不是秉耀陆续把老二圣承、老三圣传送来,交给他抚养,还真就剩他一个孤老熬日子等死。圣承生在光绪十二年,十九岁了,圣传才刚十三,还是个孩子。此刻听见院子里有响动,圣承、圣传也出了门,见长兄侄儿跪倒在地,都吃惊地面面相觑。圣衍父子一直跪着,也不肯站起来,唬得圣承、圣传忙也跪下,也不敢问所跪为何。老三义似乎明白了什么,脸色蓦地庄重起来,朝圣衍点了点头,简短地道:“堂屋说话。” 老三义说的堂屋,其实也就是寻常农家的厅堂,正中靠墙八仙桌上,规规矩矩摆着祖先牌位画像,从早到晚敬着香火;两侧各有一间卧房,分别住着老三义和圣承、圣传兄弟。堂屋本就不大,一下子拥进五个男丁,顿时显得局促起来。老三义瘸着条腿,由圣衍搀扶着落座,却也不说话,朝圣承指了指抽屉,圣承忙过来取出线香,凑在火烛边点了,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老三义扭脸看着香火,半晌没动静。烛火摇曳不定,香烟袅袅,不知何时,老三义眼里绽开泪花。他长叹一声,对着圣承和圣传道: “跪下。” 圣承、圣传慌忙跪倒,一句话也不敢问。老三义看了看圣衍,道:“你爷爷交代的事,今天就办了?”圣衍从容跪下,叩头道:“全凭姥爷做主。” 老三义沧桑一笑道:“不是老汉我熬着不肯死,是那阎王爷知道我有事没办,不要我。我那老亲家是读书人,心眼多,抢在光绪七年先死了,倒把事情撇了个干净。” 圣承一肚子不解,道:“爷爷,您有事就吩咐,我们都听您的。” 老三义微微一笑,道:“你们俩叫我爷爷,他却叫我姥爷,个中缘由,你们知道吗?” 圣承、圣传互相一瞥,都觉奇怪。两人过继到中牟王家的事,打小就没瞒过他们,就连小一辈的徵茹都心知肚明,老三义冷不丁旧事重提,实在不知他葫芦里到底装着什么药。只听老三义慢悠悠道:“光绪三年,中牟大旱,大灾之后又是大疫,我身边子女八个,死绝了。圣衍他妈也死在瘟疫上,临了连孩子都没见上。我那女婿秉耀,后来又有了你们俩,按照我尚得哥生前的意思,过继到我死去的俩儿子名下,改姓了王,算是我的孙子。这些事情,你们是知道的。” 圣承、圣传磕头如捣蒜,圣承年纪大些,又触动心事,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他虚岁已是弱冠之年,自打三岁就被秉耀送到中牟,改姓了王,过继给了老三义死去的大儿子。这是尚得在世时定下来的,他的本意是老三义不该无后,两家又是亲家,两人还是结拜的兄弟,孩子是谁家的后人都一样。秉耀的续弦夫人杨氏,自然为此闹得天翻地覆,但也于事无补。说来也怪,以秉耀的脾气性子,尚得在世时也没见他有多听话;偏偏尚得驾鹤西游了,他倒成了不违父命的孝顺儿子,送走一个还不够,几年后圣传出生,依旧是送到中牟王家。两兄弟年纪相仿,经历相似,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本就亲近;而圣衍年纪大他们不少,又远在郑州,往来不多,便日渐疏离。光绪二十五年秉耀去世,圣承、圣传到郑州奔丧,竟不得以沈家后人的身份参与,气得杨氏当场吐血,一年后也撒手人寰。往事如此,圣承兄弟难免心有块垒。圣传生性孱弱,倒还好说,而圣承却颇肖乃父,心思活泛得多。四年前两宫回銮,路过中牟,自是倾全县之力迎驾,县衙出榜征召民夫修缮官道馆阁。圣承那年才刚十五,偷跑去了工地,每天出工收工挣工钱不提,手上也没闲着,顺回家不少零碎,时间一长,胆子越来越大。也合该出事,那天知县视察工地,丢了颗珠子,阴差阳错被圣承捡了。知县丢东西不是小事,衙役们如临大敌,把整个工地翻了个底朝天,逐一搜身清查。圣承也是狡黠,把珠子塞到肛门里,竟逃过一劫。坏就坏在他到底年少,不懂避风头,悄悄到县城当铺换钱,被衙役守株待兔捉了个正着,人赃并获,当即押入大牢。老三义听了噩耗,倒也不慌,托人捎信叫来圣衍,祖孙俩合计一番,花钱买通了知县的师爷,上上下下打点之后,时隔小半年才算把圣承捞了出来。经此劫难,圣承老实不少,却也暗中有气,尤其对圣衍越发不满。都是秉耀的儿子,凭什么圣衍就能在郑州读书考功名,他就只能在官渡乡下种地?嘴上说是救人,却又让他在牢里待那么久,受尽殴打屈辱,说到底还是没把他当成亲兄弟。 圣承心里乱成一团麻,只听见老三义话锋一转道:“可有些事,你们俩是不知道的。”说着,他扶桌角站起,一瘸一拐来到门边,把墙角的笤帚簸箕踢开,转身朝圣衍点点头,指了指墙角。圣衍膝行过去,手指插进地面青砖的缝隙,用力抠动,将青砖一块块拿起来,再将其下浮土抓开,露出一块黑黝黝的板子;掀开盖板,下面小穴中赫然是一个不大的布包裹。年长日久,包裹已有些腐朽败烂。圣衍颤着手拿起包裹,举过头顶,呈给老三义。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不但是圣承、圣传兄弟,就连徵茹也是瞠目结舌。老三义朝半空拱了拱手,道:“尚得老哥,咱俩亲家一场,又是结拜的异姓兄弟——你交代的事,今天,就办了吧。”说完,他才接了包裹,夹在腋下,又是一瘸一拐地回到桌边,将包裹放在香炉边,毫不迟疑地打开。在场人中,只有老三义和圣衍清楚,那是京师益昌号同治年间特制的千足金条,黄油纸封,一共四块,每块五两,整整齐齐码在包袱里。老三义叹口气:“这点家当,是尚得哥留下的。黄金二十两。” 圣传早看傻了眼,跪在地上同泥人无异,圣承心头猛跳,顾不得旁边还跪着圣衍父子,当即叩头道:“爷爷,怎么分,我们都听您的。” 徵茹听见这话,总觉似有不妥,却又说不真切,而圣衍的脸色立刻严峻起来,一双眼目光灼灼,看了看圣承,又看着老三义。圣承分明是话里有话。在他心里,圣衍跟他虽不算路人,却也情分寡淡,没什么担待。以前大家都穷,大不了互不来往,如今平地冒出一笔大富贵,圣承看在眼里,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按理说,老三义也讲到金子是尚得留下的,也就是沈家的,他只是保管;而圣承和圣传名分上姓王,是王家人,说破天也分不到手。圣承之所以想也不想,脱口而出由老三义分金子,就是提醒老三义,他和圣传既是王家之后,也是沈家儿孙,这笔钱自然不能全归了圣衍。 7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