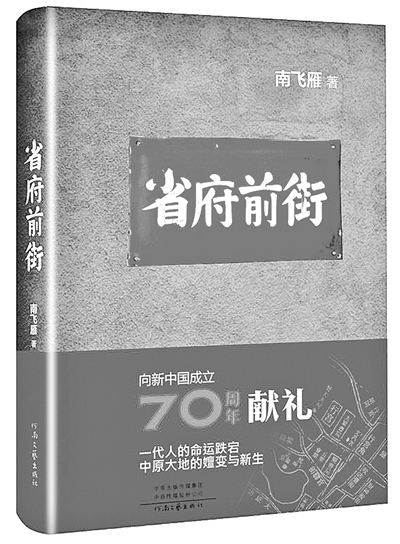|
| 第11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徵茹一咬牙,点头道:“文小姐莫再取笑,我自然是没什么退路的。” 惠葳脸色微变,一边啜着茶,一边感慨道:“那就——有些委屈你的Eva了。”又微微冷笑,道:“这就不要她了吗?也罢,男人都是这么无耻。”说完,她便沉默起来,直到散场再也没有开口。 过不两天,圣衍打电报给徵茹,电文曰:婚事谈毕,速回。徵茹看过电文,又低头看着桌上的信,一时间百感交集。信是给金小姐的,几易其稿,刚刚写完。信上措辞斟酌良久,哀婉而有分寸,决绝又不薄情。纵然再被惠葳看到,也不至于让她瞧不起。多年之后,徵茹偶然读到一首诗,其中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句,当年给金小姐写诀别信的场景便油然浮现在眼前。又过两月,正是沈、文两家议定的吉日,徵茹和惠葳在郑县完婚。婚礼那天,婚宴办了两场,中午一场是旧式的,来的是沈家的亲友故交;晚上一场是西式的,特意从开封的美美番菜馆请来了意籍大厨,喜宴就设在沈宅,招待徵茹和惠葳遍及全国的同学同年们。也幸亏郑县守着平汉、陇海两条铁路,不然往来还真不便利。惠葳是在上海读的女中,同学自然都是女的,此番或是呼朋引伴,或是携家带口,来了不少。西式婚礼本就热闹,在场的又都是年轻人,比起中午礼节烦琐要轻松很多。惠葳时年十九岁,虽不是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的,却也是靠前的几个,而且年纪算小的,所以好几个女同学都拿她起哄,怂恿她和徵茹报告恋爱经过。徵茹一肚子苦水哪里能讲,便笑着打哈哈,恨不能立刻宣布婚礼结束,惠葳倒是大大方方坐着,任女伴们撺掇嚣嚷,一会儿是笑眯眯看着她们,一会儿是笑眯眯看着徵茹,惹得女伴们不依不饶,非要她讲。到最后惠葳见实在躲不过,便站起来,笑道:“你们就这么不给人家沈先生面子吗?真要如此的话,我就诵一首诗好了。是沈先生特意引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字叫作To Eva。” 席间一片惊愕唏嘘之声,一个圆脸的女孩子便嚷道:“这也是奇了,是Emerson事先知道你叫Eva,还是你家沈先生特意找到的这一首?” 满座笑语不绝,掌声丛起,徵茹惊得差点跌在地上。只见惠葳款款站起,看着众人,开始了朗诵,最后把目光定在徵茹身上,只听得她清声朗朗道: “Ah! Let me blameless gaze upon,features that seem at heart my own;nor fear those watchful sentinels, who charm the more their glance forbids,chaste-glowing, underneath their lids, with fire that draws while it repels.” 夜半尽欢客散,早有沈家雇下的汽车马车候在门外,将客人一一送到旅馆去——旅馆是沈家自己的产业,特意停业三天,专门接待少东家少奶奶的客人。宾客们甫一离开,圣衍和周氏就差人传了话来,说天时太晚,不必过去请安了。惠葳觉得不妥,坚持跟徵茹去问安已毕,这才躬身退了出去。圣衍自是志得意满,忍不住道,毕竟是大家闺秀,尽管喝了些洋墨水,礼数还是懂的。周氏是儿子婚事的始作俑者,心中也是喜不自胜。徵茹和惠葳离开后宅正房,朝自己的新房走去。月色正好,两人一路上走得很慢,过一簇冬青之际,徵茹到底还是捉了惠葳的手,扣在掌心里。惠葳倒也不躲,任由他牵着,并排踟蹰向前。说来也怪,分明是院子里人少了,却比刚才宾客林立时还显得拥挤。夜穹也低得吓人,明月就在头上,仿佛伸手可触的样子。到处的树影花草间,似乎有数不清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看着两人,而且视线越来越近,像是生生地把他们挤在一处。行了数步,徵茹停下来,道:“今天那个女子,就是戴一副眼镜,脸圆圆的,跟你说什么来着?见你笑得很舒心。” 惠葳想了想,道:“说起一个人,那人也是可笑得很,为了一个所谓买办的女儿,伤了另一个痴心的女子,到头来东床快婿也没做上,只好灰溜溜回原籍去了。” “这倒真是可发一笑了。”徵茹微笑道,“我见你那些女同学,穿戴发式,大约都是京沪间最时兴的,确是比中原腹地得风气之先——你若是喜欢,不妨订些画报周刊的,平时解解闷也好。” 惠葳笑起来,道:“这个我自然有门路,那些东西都是走火车的,陇海铁路上有文家租的厢位,每月两次走津浦路、沪宁路运货,捎点画报之类很方便。” “文家的花生棉花里,放上几册画报周刊的,倒也是一景了。” 两人不觉都笑了起来,便继续前行。惠葳忽然道:“开封往海外发邮件邮包,走的也是这班车。不然,我怎么能知道什么To Eva呢?”徵茹心里一动,便道:“你洋名叫Eva吗?怎么从没听你说过。”惠葳狡黠一笑道:“我刚看见的时候,也是要惊掉下巴的,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难道她的洋名也是这个?”徵茹尴尬摇头道:“自然不是——不过也难为你背得那么好。”惠葳低头喃喃道:“能不背得好吗?翻来覆去看了那么多遍的。”说着,惠葳停下来,像在斟酌着什么,徵茹也停下,耐心地看着她,等她说出来。所谓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人。夜月之下,惠葳静静地立着,缓缓仰了脸,看着月亮,看得一双眼里月色撩人,却也不知不觉荡漾起了水痕。徵茹一怔,分明看见有两行泪,就那么从她眼里的月色中淌了下来,顺脸颊缓缓坠下,融入了更深的月色里。好半晌,惠葳方才扭过头,见他脸上又是认真,又是关切,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怎么办?其实你不爱我,其实我也不爱你,偏偏你我就这样了。往后日子那么多,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徵茹一时无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用尽手段瞒着金小姐的事,自以为得计,却被惠葳拿一封信拆穿了。而惠葳也用尽手段,又是截下他的信,又是逼他跟金小姐分手,到头却不得不嫁给他,做了沈太太。两人心里都有另一个人,或者说,都曾有另一个人,也都不知道这个人会留在心里多久。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只有这个人走了,才会容得下面前的人。夜色正长,路却到了尽头。一阵挂着清凉月辉的夜风吹过,两人身子都是悚然一晃,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时,却发现已然站在了新房门口。 11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