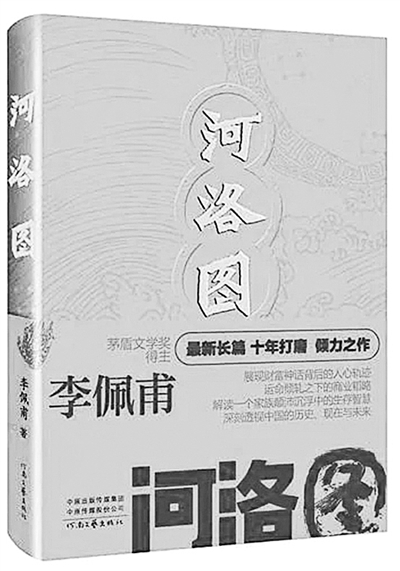|
| 第03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那年月,每到汛期前,河洛交汇处就会聚集大批的青壮汉子,他们都是来吃河饭的。河口的旗杆上升上龙旗,吃河饭的人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漕运是京城的命脉,加上黄河年年决口,治河投入巨大。每每汛期来临之前,圣旨一道又一道从京城发来,严饬河官查看河道,有淤积处,迅速挑浚疏通,以防酿成大祸。因此一到汛期,水官们就格外地小心。 龙旗升起,吃河饭的汉子们,在河官们的带领下,分成十人小队,一队一队领牌上工。这时候,河堤上还会升起两种旗帜:一为“号旗”,相当于队伍的编号。十丈一小旗,百丈一大旗,领工的是河兵。还有一种旗是专用于施工时发号施令,这叫“标旗”。施工到了紧要关口,若急需土方则升黄旗;需用木料则升红旗;用柳条、蒲草则升蓝旗,夜间则改为三色灯笼……急迫时,锣声四起,号子如山岳,一排一排的人墙,与那滔天浊浪抗争。 那年夏天,端午过后,河洛口的大堤上,在蚂蚁一般的河工队伍里,出现了一个奇人。开初时,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打眼的地方。在赤裸着上身的汉子群里,他只是中等偏上的个头,看上去黑黑的,没言语。人也就三十壮岁,一条辫子盘在头上,穿一件对襟的粗布汗褂,腰里扎一根毛蓝布带子,显得肩宽腰细,周正利落。若细看了,只是眉眼紧,走路轻些,别的就没什么了。 可一上工,干起活来,差别就出来了。同样是在河堤上运送木料,丈二的圆木,二里半的路程,别的河工两人抬一根还略显吃力,中途要歇上一哈儿。他却不然,头一趟他就一人扛了一根。这倒还罢了,到了换牌子登账时,听河官说扛一根两个铜子。于是到了第二趟,他左胳肢窝夹一根,右胳肢窝夹一根,竟然一人运两根。走起来,依然健步如飞。 顿时,一河的人都看傻眼了。说这人谁呀?好神力! 河上人多,眼杂,嘴也多。人们打听来打听去,才知道这人姓马,叫马从龙。是前不久从外乡流落到河洛镇的。 到了第三天,人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鸟人,怎么这样呢?人家两人抬一根,他一人扛两根。一个人就挣了四个人的钱,河上的钱都叫他挣了。这且不说,中午吃饭,发的黑白两掺的馍,他一串叉四个,两根筷子就叉八个,那是杠子馍,他一顿吃八个! 最先看不上的是洛寺村的人。洛寺村离河洛口最近,一姓的族人多,人头旺,也就霸道。他们常年吃河饭,看这狗日的一顿吃八个杠子馍,钱也都让他鳖儿挣去了,于是一个个躁躁地,嘴里骂骂咧咧,很有些气不忿。这些人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嚷着嚷着火上来了。河堤上人多,况都是壮汉,经不住这么起哄架秧子,不知那个愣头青先开了口:奶奶的,走,打他个小舅。 倏忽间,就见河滩里刮起了一股旋风,一时群情激愤,人们黑压压地涌过来了。挑头的自然还是洛寺村人,人群里有狗叨毛架鹰撵兔打哄哄的,有看热闹递小拳骂阵的,乱嚷嚷聒噪噪一片喊打声。 立时,就见河滩里尘土飞扬,唾沫星子四溅,荡荡黄尘里一片乱麻麻的黑脊梁,一窝蜂似地扑将上去,那胳膊犹如一片棍林,斜刺里乱马绞枪像是长出了无数条铁腿……渐渐地,人就看不见了,只有一团一团的黄尘在河滩里滚来滚去! 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终于有人醒过神来,喊道:别打了!别打了!再打出人命了! 这时,有河兵跑过来,嚷道:干什么?干什么?想闹事啊?! 人们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全都住手了。河滩里顿时静下来了。往下呢,往下就不敢想了。那人呢,恐怕打死个球了。成肉酱了吧? 当管河工的千总带着护卫赶来时,人们才知道害怕,慢慢地往后退去,让出道来。黄尘慢慢散了,只见躺在地上的那个人,那个叫马从龙的人,已经被黄尘埋了。 过了片刻,又见那土沫子慢慢往上冒,冒……人们小声说:动了。他动了。 又一会儿,渐渐,一个人头从土里冒出来了。马从龙先是慢慢坐起身子,噗噗吐了两口土沫子,继而,他爬起来了,还拍了拍身上的土。居然、他居然安然无恙?! 千总吃惊地望着他,说:喂,小子,你没事吧? 马从龙略略点了点头,嘴里又徐徐吐了一口气,说:不当紧。 有河兵把他架起来,说:走两步,走两步。 千总惊呆了,说:你……你真没事? 马从龙四下看了看,突然看见河滩里摆着一个夯土的石磙。他当着众人走过去,弯下腰,默默地吸一口气,“嗨”的一声,双手把那石磙举了起来! 一时,整个河滩静得嚇人。人们默默地望向他。就此,再也没人敢找他的麻烦了。 二 分家后,周亭兰带着儿子,悄悄地搬到镇上住了。她先是在店铺后面一孔窑洞里凑合了些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她一直在寻访能给儿子治病的人,找过几位中医先生,也请过神婆,扎针许愿、烧香上表,都不管大用。 没住多久,她就搬了。儿子看着她,那神情像是在问:刚刚住下,为什么要搬呢? 周亭兰说:儿呀,我怕伤了你的耳朵。 原来,店后面的窑洞里住的大多是走水路和旱路的纤夫和脚伕。他们卖苦力挣了些钱,可他们夜夜赌博,把好不容易挣来的散碎银子又输出去。况且这些人在输了银子喝了酒之后,还会闹些事端。叫骂声、吵闹声不绝于耳,且一言不合,打得一塌糊涂。 周亭兰说搬就搬,她带着儿子搬到不远处的唐家胡同。这是个很干净的小院,隔墙院里还种有花草。然而,仅住下没有几日,她又搬了。 年幼的康悔文不知道,这地方的后墙离常春院太近了。常春院白天里静静的,一到晚上,夜夜笙歌,蜂浪蝶舞,成了一锅花粥。不时地,有老鸨高喊:客,花俩吧! 那日,周亭兰从店里回来,康悔文突然说:娘,给我买只兔子吧。周亭兰一愣,说:这晚了,哪有卖兔子的?儿子说:后边院子里就有卖的。老听人喊:兔儿,兔儿的,还问要大白还是小白……周亭兰一听,脸色陡然变了,厉声道:胡说! 然后,周亭兰二话不说,立刻又要张罗搬家。她说:儿呀,我是怕伤了你的眼啊。 河滩上闹事那天,周亭兰刚好带着伙计往河滩上送蒸馍。听河工们议论河滩的奇事,她心里寻思,这不正是她要找的人么。于是,她立刻托人打听了马从龙住的地方。第二天傍晚,提了两匣点心,她就到马家去了。 2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