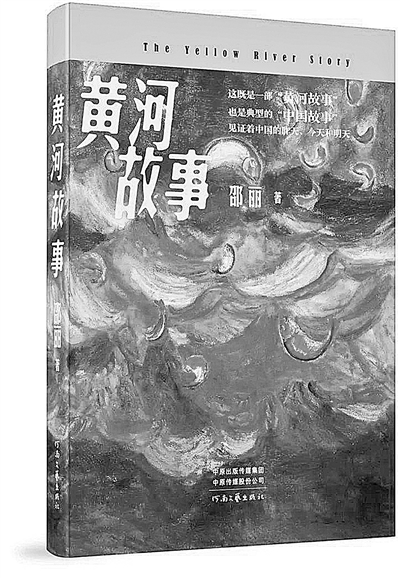|
||||
上学之后才听村里的老辈人说,我爷爷和我姥爷是世交。爷爷是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写一手好字,开的药方都被人当字帖用。姥爷家境富裕,是三村五里闻名遐迩的乡绅,也写得一手好书法。两个人到一起,就是写字、下棋、喝酒。据说我爷爷最佩服的人就是我姥爷,说他人仗义,事儿做得公道。要是没有我姥爷主持公道,村子早就乱得没有章法了。 母亲从未说起过他们,父亲也没说过。只是有一次我大姐争强要求入团,学校老师说了句难听话:回家问清楚你们家的社会关系再说!我大姐哭着从学校回来问我母亲:“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姥爷,让我们什么事儿都干不成?”这是我家的忌讳,似乎从没人提及这个话题。我大姐是仰仗着在我母亲跟前得脸,恃宠而骄。我们一家子人都被她吓住了,那一会儿安静得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见。我预感会有一场山呼海啸,母亲会不会恼羞成怒?我甚至期待,这顿暴打终于不是落在我身上了。谁知道,我正在纳鞋底子的母亲突然抬起头来,竟然显出一脸的自豪。她稳稳地瞧着我大姐说:“你姥爷,一辈子可真没白活!”后来听我二姨说,枪毙我姥爷的时候,正在上中学的母亲就穿着上白下蓝的学生装,站在距她爹很近的地方。枪响之后,血沫子顺着风扑了我母亲满脸满身,她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爷爷也没白活!他跟你们姥爷一样都是体面人。”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你姥爷拄着拐棍儿往村里一站,那没有不听他说话的。再大的事儿,他只要站那儿三说两说,什么事儿都摆平了。” 父亲出走的那天夜里,天气非常恶劣,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们早早就上了床。半夜里我们突然被他们房间发生的激烈争吵弄醒了,当然主要是我母亲在嘶吼,然后就听见有什么东西被打碎和我弟弟惊恐的哭声。我们姊妹四个的房间与父母隔一间堂屋,他们住东屋,我们住西屋,弟弟跟着他们睡。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除了听见外面的风声雨声,夜晚屋子里静得吓人,仿佛能听见我们几个的心跳。不过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起来看看。刚开始的时候,被惊醒的小妹吓得想哭,大姐在她脸上狠狠拧了一把,她缩进被窝里再也没敢出声。鸡叫头遍的时候风雨停止了,我大姐那边传来细微的鼾声,大家逐个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发现父亲不在了。第三天,第四天,天气转晴了,万里无云,世事一派祥和,但我们再也没见到父亲。他在与不在,都不会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 母亲依然忙里忙外,操持着一家人的吃喝。我们没有一个人问起过他,好像家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似的。 第五天早上,我们还在梦里,就被母亲一个一个从被窝里拽起来。她让我们立马穿上衣服,往我们每人头上和腰里勒上一条白布,冲着我们喊:“都出去哭去吧,你爹死了!” 二姐听了,坐在床上哭了起来。母亲一把把她拽起来吼道:“哭什么?要哭去后面好好哭!”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好大的怒气,却没有一点儿伤心。 那时我刚从二姨家回到这个家不久,心里根本不知道害怕。我们跟着母亲,来到屋后的院子里,看到院子中间的席子上躺着一个巨大的尸体,被水泡得像一头牛,浑身散发着说不出来的腐败气味儿,头肿胀得像一个粪筐那么大。这怎么会是我们清秀俊朗的父亲呢?我们都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母亲不由分说便把我们一个一个按跪下,然后就号啕起来。我们扭头看着母亲,她听不见我们的动静,移开捂在脸上的手巾,拿眼睛狠狠地剜我们。我们只好也学她的样子,跟着半信半疑地号哭起来。但我哭了一会儿,觉得泪水真的出来了。 二姐只是默默地流泪。 在我们村子里,我们这个姓氏是一门很小的人家,没人出头管事儿,再加之父亲又是横死,所以也没举办什么葬礼。我们哭了一场,就把父亲草草送到火葬场了。 事后偶尔听到母亲跟村上的人诉说:“黄河水那么凶险,哪一年不淹死一堆人?”在母亲的话语里,父亲是趁下大雨到黄河里捞鱼,被大水卷走了。再后来,母亲说起这事儿的时候,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几句:“摔死的都是会骑马的,淹死的都是会洑水的。许是饿死鬼托生的,怎么那么贪吃呢?” 此次之后再说起父亲,她都喊他“饿死鬼”。 我那时候懵懵懂懂的,听了母亲这话,真是觉得父亲是自己找死。他是太贪吃了,下那么大的雨去打什么鱼呢?除了二姐,本来我们几个跟父亲也没多少感情,他死了也就死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们甚至还有点庆幸,家里的空气应该不会再那么紧张了吧? 几十年后,母亲给父亲选择了黄河边的邙山墓地。母亲说,你爸活着的时候喜欢去北边的黄河打鱼,就葬在那里。我也觉得那个地方不错,人家的广告语就是“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虽然那个北邙说的是洛阳,但是邙山东西狭长,郑州北郊黄河边的邙山的确也属于北邙。 我找了好几个老同学,他们还都在管事儿的位置上,但是价格怎么也压不下来,一块儿墓地五十万已经是最少的了。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墓地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而邙山墓地更是寸土寸金。完全可以把孔圣人那句话改成“不知死,焉知生”了。 母亲想把父亲安置在这里,不知道考虑了多长时间,肯定不是突发奇想,但也不会谋划很久,她是个心里存不住事儿的人——只有父亲死亡的事情除外,那是她的黑匣子。也许父亲根本就没什么事儿,是我们多想了。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促使母亲做出给父亲买墓地这个决定的呢?她是突然想到还是悟到了生命中的某个东西? 我母亲看上去很累,仿佛是一夜之间苍老了。 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给大姐二姐和弟弟说了没有。我说虽然我的房子可以卖二百来万,但一下子也出不了手。这几年生意上连续投资,手上也没闲钱啊。母亲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打了!都打了!” 其实,开始我就知道让我们姐弟几个每人都拿钱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母亲就是想要我主动说出来,所有的费用由我一个人出。这话我早憋在喉咙口了,不吐出来,是不想让她觉得太随便。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况且各自是一家人,我可以在姊妹困难时帮他们一把,但每次把责任都推给我,显然令我不快。要是我遇着困难,他们帮不帮我,就难说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现在母亲的态度突然转变了,立场似乎也很鲜明。 1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