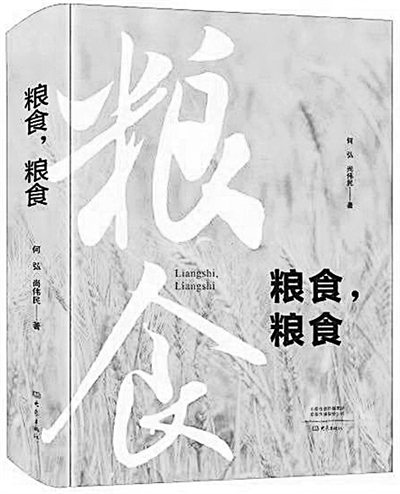|
||||
我国的早期小麦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即青海东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绝对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最早记载小麦的文字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中有“告麦”“食麦”的记载;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第 8 册,也有“正一月曰食麦” 这样的释文解说。 《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诗经·魏风·硕鼠》中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由此可见,麦在春秋时期已经广泛种植。 《诗经·周颂·思文》中有一句“贻我来牟”,“来牟”繁体字作“麳麰”。从周人赞颂他们祖先的诗篇中可知,公元前 11 世纪在关中地区就已经有麦传入了。古代所说的“麦”,是大麦与小麦的统称。今天表示“到来”的“来”是一个假借字,原本是一个象形字,就是“麦”。 具体说,“来”指小麦,“牟”指大麦。 《左传·隐公三年》记载了一个发生在春秋初期周王室与郑国之间的故事:“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说的是这年四月,郑国的祭足带兵割取了温地的麦子。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已经栽培小麦了,而且人们已懂得利用晚秋和早春的生长季节种植宿麦也就是冬麦了。冬麦的种植,有利于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 麦子在周代已经得到普遍重视。儒家经典《春秋》中说:“它谷不书, 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这说明当时人们对麦的重视程度已与粟相提并论了。不过这时候小麦一般为祭祀专用,普通老百姓很少食用。 战国时期,虽然发明了石磨,但麦子的食用并没有很快从“粒食” 过渡到“粉食”,这其中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 在中华民族的食物史上,粒食之法持续了很久。《墨子》中便称“四海之内,粒食之民”。在先秦乃至汉代,人们普遍认为粒食才是正统的吃法。而磨成面粉吃,则属于“歪门邪道”,粉食者被看作缺乏教养的化外之民。 何为粒食?比如小米、稻米,不管做成米饭、小米粥,都保留着粮食颗粒原状。即便是不好熟的豆子,吃多了还会胀气,古人也是煮粒而食。有一个形容食品粗劣、生活水平低下的词语——麦饭豆羹,说的就是把麦子、豆子直接煮熟当饭。 小麦传入我国之后,我们的祖先根据以往的经验,自然采用了与小米和稻子一样粒食的习惯方法来食用——将小麦蒸熟或者煮熟,做成“麦饭”或“麦粥”。 因为“磨麦合皮而炊之”,麸皮有苦涩味,与小米、大米相比,无论是麦饭还是麦粥,口感都相差甚远,所以,那时候麦饭或麦粥均为差等饭食,只有底层老百姓才常吃。在上层社会,倘若有人用麦饭来招待客人,就会被看作对客人不尊重。如果儿媳妇自己吃米饭而让婆婆吃麦饭,就会被视为不孝。 不言而喻,食用方法限制了小麦的推广普及。 事实上,最初的小麦品质也不好,即便是磨成面粉,也不适合制作面食。比如,甘肃临洮地区虽然很早就种上了小麦,但直到南宋,这里的小麦仍然不适合磨成面粉。史料记载,这里的小麦面粉黏牙,想要擀面条,和面的时候必须掺进去一些草木灰。现在遍及全国的“牛肉拉面”, 制作时通常都要添加“蓬灰”,即蓬柴草烧制而成的草木灰,就是为了增加拉面的口感,吃起来更筋道。 从汉代开始,石磨的普遍应用,让小麦真正得以推广和大面积种植, 且在人们的粮食构成中日渐重要。特别是在北方,麦的种植得到大力推广。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说:“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 在西汉,种植麦子已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如: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书·武帝纪》)。东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安帝“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 务尽地力”(《后汉书·安帝纪》)。另外,农学家赵过和氾胜之等也都曾致力于在关中地区推广小麦种植,汉代关中人口的增加与麦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物格局依然是南稻北粟,但麦类的种植开始普遍, 在北方大有追赶粟类之势,在南方则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也开始少量种植。 《晋书·武帝本纪》中记述,当时春小麦栽培向西扩展到甘肃陕西地区,5 世纪更向西北推进到高昌、向东北推进到勿吉。而冬小麦的栽培, 则随着北人南下而逐步向南发展,第一步向江淮地区推广,第二步向浙赣地区扩展。 唐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文化的发展、疆土的扩大、对外关系的加强,小麦的栽培范围又有新扩展,主要向西、西北和南方发展。《齐民要术》记载,粟居首位,麦、稻则稍后于粟。而在《四时纂要》中,粟、麦、稻已并称,说明这个时期麦的种植比前代更加普遍了。 一直到唐代中期,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地位并不突出。随着唐朝与西域各民族的交流,粉食虽然已经被人们接受,但当时流传一个使小麦面粉被歧视的致命传言,那就是“面毒说”。为此,唐代的《新修本草》专门辟谣,明确说小麦无毒,但当时一些权威“专家”仍言之凿凿称其有毒。唐代名医孙思邈认为,面“多食,长宿,澼加客气。畏汉椒、萝蔔”,也就是吃面多了,易引发外邪侵入体内,用花椒、萝卜方能克其毒。孙思邈大师还说,他曾亲眼见过一些吃面多的山陕人小腹发胀,到最后头发脱落而身亡。 宋代人认为面吃多了会上火、长疮、肿腮帮子、肠胃功能紊乱,不是便秘就是腹泻。此时的《证类本草》称:“小麦性寒,作面则温而有毒。”五代十国时南唐大学士张洎和北宋医学家董汲、科学家沈括等名人都相信小麦面有毒。 南宋时,金兵曾在一次南侵撤退后留下了很多小麦,南宋军民虽食物匮乏却不敢吃,因为当时“麦有毒”的说法影响很大,人们惧怕中毒。 元代名医贾铭称,吃面粉中毒后不仅脱发,连眉毛也会掉光。 明代慎懋官在《花木考》中称:“小麦种来自西国寒温之地,中华人食之,率致风壅。小说载中麦毒,乃此也。昔达磨游震旦,见食面者惊曰:‘安得此杀人之物?’后见莱菔(萝卜的古称),曰:‘赖有此耳。’ 盖莱菔解面毒也。” 清代文学家袁枚本来很喜欢吃面,无意中从古书上看到“面粉有毒”,从此不再食用,做客时别人请吃面,必用清水反复冲洗数遍,才敢吃下去。 关于面粉中的毒从何而来,大致有两种意见: 其一,与种植地相关。南方小麦有毒,北方小麦无毒。比如,元代贾铭《饮食须知》中便说:“北麦日开花,无毒。南麦夜开花,有微毒…… 勿同粟米、枇杷食。凡食面伤,以莱菔、汉椒消之。”元代名医李鹏飞也认为,多霜雪处,面即无毒,故南方不宜种麦。 其二,加工方式致毒。唐代名医孟诜认为:“为磨中石末在内故也, 但杵食之即良”,即磨面会有石粉融入面粉,有毒,但用杵捣加工面粉就无毒。 6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