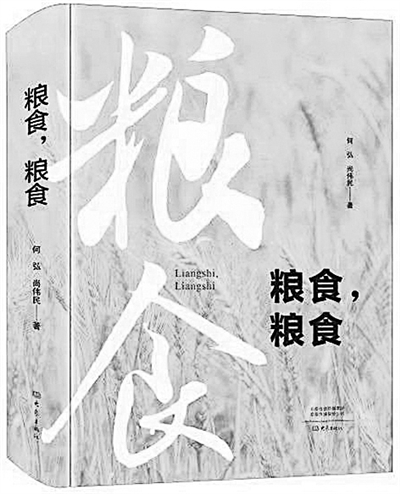|
||||
为了增加收入,多挣工分,无论是尚本礼老师还是他的爱人祁青芹社员,都尽可能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产队也鼓励在外工作人员、民办教师、中学生星期天和节假日参加田间劳动。 每个社员的劳动工分值,都是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上讨论评定的。工分评定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因素也相当复杂,与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劳动能力、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都有关系。 尚本礼老师参加过本生产队评分的社员大会,大致情况是:正常的生产劳动,一般青壮年男劳力,早上(3分)、上午(3分)、下午(4分)一天三晌出全工,挣1工(10分);老年男劳力 8至9分;14岁以下少年劳力,一天5至7分;15岁到17岁少年劳力,一天6至8分;青壮年妇女,一天8分;老年妇女,6至7分。 比如看护庄稼地,比较轻松,大多都派老人干,一天8分;像浇地, 虽然轻松,但开柴油机或电力水泵,都需要技术,还有夜班,都是年轻男劳力干,一天工值就是1工;再比如赶牲口的把式,技术性高,也是一天1工;挑大粪(从各家各户用木桶把人粪尿挑出来集中到一起),劳动强度大、脏,虽然松散,一天也是1工;而烧红薯炕(红薯育苗的小面积园圃),比较轻松,技术含量也不高,一天8分。 冢后大队第三生产队就因为烧红薯炕出过“典故”:这年开春,第三生产队开会评工分,队里派一个绰号叫黑椹的老先生负责烧红薯炕。黑椹五十多岁,上过私塾,有文化,还当过几年兵,身体瘦弱, 一般的农活都干不了,生产队为了照顾他,就派他干一些看地、烧红薯炕这样的轻活儿。评到黑椹,队长说,烧红薯炕这活儿轻松,一天烧两回就中了,一天也按8分。黑椹觉得不公平,就说,烧红薯炕轻松是轻松, 可这是技术活儿,还得操心,不评一工三吧,最少也得跟整劳力一样, 评一工吧。队长看看社员,大家都不说话,最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如果黑椹顺利完成这项任务,这事就不会成为冢后大队“风光一时” 的著名事件了——半个月之后,黑椹老先生把红薯全烧熟了,不得不把红薯种扒出来分给社员们,成为一个笑话,并由此诞生了冢后大队独有的一条歇后语:黑椹烧红薯炕——那是技术活儿。 祁青芹社员很能干,是妇女劳力中工值最高的,一天8分,早上2分,上午3分,下午3分。因为要带孩子,早上基本上是没法出工的。中午要给孩子做饭,得提前收工回家,也会扣工分。中午打发孩子吃完饭,弄不好又会误了下午上工。加上她自己再有个头疼脑热、不舒服, 没法上工,一年下来,能挣到的工分也不过五六十工,折合成钱也就是10 元多点。 尚本礼老师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是个教书先生,劳动技术不够, 也吃不了太大的苦,生产队为他评定的工值是一天8分。扣除冬季没有农活的星期天、假日,他满打满算能参加劳动的总时间也不超过两个月, 加上学校或家里有事不能参加劳动,一年最多也只能挣到三四十工,折合成钱8元左右。 两个人挣的工分钱,加到一起还不够“缺粮款”的零头,但毕竟还是可以补一点亏空。再者,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这至少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也让那些天天在地里干活的骨干劳力心里舒服一些。 曾经的温饱生活 新中国成立那年,尚本礼老师家按人口分了10多亩土地。他的父亲是革命干部,曾上过西学,是最后一批民间所称的“洋学秀才”,民国时期做过公学教师、联保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政部门、供销部门工作。他的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好手。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打理土地,还做加工生意,一家子的生活很殷实。 尚本礼老师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哥长他5岁, 自小就上学,从私塾一直上到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十几岁即离开家乡,大学毕业后留在省会工作,与土地基本没有直接关系了。尚本礼老师自幼身体壮实,脚大手大,用坊间的话说,一看就是个能掏力的坯子,父母也打算让他继承祖业,在家种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豫北田地里的井还很少。那时候,土法打井全靠人工挖掘,方法也笨:先在地上挖掘直径两米左右的圆筒,挖到一定的深度,就在井底放一个中间空的圆木盘,然后在木盘边缘上砌砖,砖砌到地面,再继续下挖。接下来的工程非常缓慢和艰难,要一点一点地从木盘下边掏土,再用木桶把土拉到地面。掏土的过程中,必须让承载着井壁砖的木盘保持平衡,一旦倾斜,砖坍塌下来,下边的人轻则受伤,重则丧命,搞不好就会倾家荡产。再者,还存在挖到很深而出水量太少甚至无水的可能,那就白折腾了。这些风险,使打井的成本过高,与浇水带来的效益相比并不划算,加之长期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靠天收”观念,人们打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冢后村曾流行过一个关于打井的“典故”:尚超峰打井——“泼” 上了(即拼尽全部财力的意思)。尚超峰是尚本礼老师远门的一个叔叔, 读过私塾,在村里也算个文化人,家里的地靠天收成很差,就踅摸着打一口井。这一年春天,打井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动工前,尚超峰对打井师傅和帮忙的人承诺:这次打井,“泼”上了,无论师傅和忙工,吃饭保证“一块面”,完工后炸面坨管吃饱。开工之后,生活标准却打了折扣,只中午一顿饭让吃馒头,早晚饭全是红薯干面、玉米面两掺窝窝头。令大家更失望的是,完工之后的炸面坨,更是没见影儿。人们对尚超峰“放空炮”自然不满,便以戏谑的方式赠送给他一个歇后语式的“典故”。每每有人说到要自己或别人下决心放开花钱,就会用上那个“典故”:尚超峰打井——“泼”上了。 没有井,种庄稼全靠担水浇灌,效率极低,给三五亩地浇上一次水, 得全家能干的人都拼命干几天。 尚本礼老师的母亲,那时候已经认识到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很重视给土地施用肥料。他们把豆饼、棉油饼砸碎埋在地里,肥力更好, 他家的庄稼比周边的长得明显好,收成也能高出两三成。 尚本礼老师还记得,每年的夏收和秋收,母亲都要亲自操持留种子的事情。母亲说,好种出好苗,好树结好桃。留种的事一点都不敢马虎。尚本礼老师后来才知道,母亲这句话是中原地区的农谚。 尚本礼老师家的小麦种子,都是多年传下来的品种,主要是“小红芒”“大白芒”这两个品种(民间把“芒”读作王)。“小红芒”产量略高,但磨出来的面发黑,口感也略差。“大白芒”磨出来的面白,口感也好, 但产量低。一般的农户,对两种小麦品相、口感的差别并不在乎,最大的愿望是收成好。因此,在华北平原乃至西北、东北地区大面积的麦田中,“小红芒”所占的比例绝对主流,而“大白芒”大多是一些大户自给自足的品种。 选小麦种子相对简单一些。收麦之前,选择土壤肥沃、长势均匀、品相良好、株壮穗大的地块,先把参差不齐的杂穗拔掉以保持纯度,再适时浇一次“麦黄水”。浇“麦黄水”主要是为了促进籽粒饱满,提高麦粒质量。再者,可以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地温,减轻干热风的危害。做种子的小麦要单收单打,晒干后单独存放。 20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