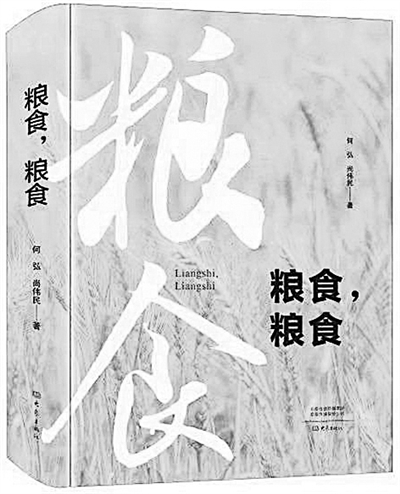|
| 第07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1949年,全国只有132个城市,城市人口不足4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3%。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57年底全国城市人口已超过7000万,总占比上升到10.9%。尤其在“大跃进”期间,通过“大招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干部数量猛增。到1962年,城市人口超过1亿,总占比达到15.4%,加上小城镇人口,总占比已接近 20%。 一方面,城镇人口增长过快,加重了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减少,积累的基础被削弱,无形中减少了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只能从源头上加以限制。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精简领导小组。短期内,全国国家机关职工裁减了35%,由268万余人减少到174万余人。 不能按时开学,尚本礼老师一下子懵了。回到村里,父亲已经结束养病,向省里提出带病工作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一个离家近20里的公社供销社工作。 父亲每月的粮食“定量”勉强够他在单位吃。三弟和妹妹因为生活困难已从当地民中退学,四弟12岁,上完小学,也该升初中了,饭量也赶上了成人。尽管父亲的工资不低,但全国到处缺粮,没有“指标”和粮票,拿钱也买不来粮食。村里的“大伙食堂”已停办,生产队的仓库里除了种子再无别的存粮。家里有三个正长身体能吃饭的孩子,母亲天天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而发愁。 家里本来就缺粮,尚本礼老师又突然断了“口粮”回到村里,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和弟弟、妹妹们天天饥肠辘辘,被饿得面黄肌瘦、少气无力。一天,三弟与四弟因为争夺一块甜瓜发生冲突,三弟动手打了四弟。倔强的四弟要去陕西逃荒,非常坚决,无论母亲怎么劝说,都要走。万般无奈之下,母亲给父亲捎信,父亲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谁也不知道这样挨饿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与其在家挨饿等死,还不如跑出去讨个活命。 尚本礼老师负责送四弟去陕西,尚本礼老师的一个近门大姐一家在那里安家落户,最主要的是那里能吃饱饭。具体的地址是陕西省渭南地区韩城县坊镇公社太里大队。 说是逃荒,其实就是给四弟找个人家。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还不能靠劳动养活自己,根本不可能独立门户;又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上门入赘也无从谈起;只能委身于人,换句话说,被人家收留,做人家的养子。临别,母亲平静地说:儿啊,啥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其实她心里清楚,四儿子这一走,就成了人家的人。当尚本礼老师带着四弟走出家门的时候,坚强的母亲独自落泪。直到30多年后,母亲说到四儿还不能释怀。 1961年初秋,尚本礼老师与四弟尚本哲背着母亲为他们准备的行装, 踏上了西行的路。行装内,除了被褥、衣服,还有吃的。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留足路费和四儿短期的花费,剩下的20多块钱全给他们买成了馒头和油饼——这是冒着极大风险(如果被发现,要把东西全部没收)买来的“私货”。 村里有一个30多岁的光棍儿,穷得房子没有一间,老娘死后再没有任何亲人,住在临街的庙里。一个穷光棍,天不怕地不怕,三年困难时期时不时地从外边搞点“私货”在村里高价倒卖,馒头四块钱一斤,油饼五块钱一斤。只有在家里有重病号或上了年岁的老人好多天不沾粮食再饿下去就要丧命的时候,才舍得偷偷买点馒头、油饼来救命。大队干部对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步行,坐汽车、火车,路上要走几天,母亲又想方设法,做了一些掺少许玉米面、红薯干面的菜团子。父亲从自己的口粮中为他们抠出几斤粮食,又想办法兑换成全国流通粮票。在严重缺粮、几乎人人挨饿的时期,他们的旅途能有这样的“干粮”,算得上非常“奢侈”了。 根据大姐的地址,尚本礼老师查了地图,觉得韩城县属于渭南地区,应该先到渭南,然后再依次到韩城县、坊镇公社、太里大队。于是,他们凌晨5点即出发,步行60里地到滑县县城道口镇,这需要3个多小时。滑县到新乡的汽车一天只有一班,晚了就赶不上了。坐汽车赶到新乡,他们吃上一点干粮,再坐汽车赶到郑州,然后乘火车去渭南。 时隔近60年,尚本礼老师如今已经记不清什么时间坐上郑州至渭南的火车,感觉一路上都是紧紧张张。到渭南之前,是比较顺利的。从渭南到村里,却吃了不少苦,因为渭南到韩城县不通汽车,只能步行。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步行了3天才到。夜里,他们不舍得住店,就裹着被单睡在路边。饿了,吃口干粮;渴了,讨碗凉水。当他们赶到大姐家里时,四弟累得趴在地上就睡着了,脚上全是泡。 尚本礼老师给大姐交代好四弟的事,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就道别返回。他不能在大姐家多住。他一个壮小伙,饭量又大,谁家的口粮都不宽裕, 多吃一顿对人家都是负担。 回来很顺利,按照大姐的交代,尚本礼老师步行20里地即到了山西省侯马市,在这里可以乘火车直达安阳,虽然要向北绕一些路,却快得多。安阳和新乡离道口的距离均是69公里,坐汽车也方便。 回到家里,尚本礼老师蒙头睡了一天一夜。他把四弟丢在大姐家里, 一路上奔波劳顿,连伤心都顾不上。几个月之后,四弟被东雷村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收为养子。从此,四弟尚本哲成了坊镇公社东雷大队社员薛民星,与家里隔山隔水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四弟离开东雷村, 在华山脚下的一个制药厂工作,生活稍微宽裕些后,总是节省出一些粮票邮寄给尚本礼老师。 在家务农的那段时间,尚本礼老师天天还盼着开学返校的通知。但最后盼来的不是返校通知,而是滑县师范学校停办的消息,学校是回不去了。也就是说,已经成为国家体制内人员的尚本礼老师,成了一个回乡的农民。曾经对未来充满希望、踌躇满志的尚本礼老师,一时间情绪低落到谷底。他在村里感到非常压抑,想逃离家乡,而且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到大队开了一张到陕西投亲的介绍信,去滑县城关公社赵庄大队找到了比他低一届的同学王臣起,再次踏上西行的旅途。 尚本礼老师的想法很简单,去陕西找个地方,他们年轻有文化,到那儿做个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长,再不然找个家做上门女婿,总会有个活路,比闷在家里强。王臣起与他的心情一样,听他一说,二话没说, 提上行李就跟他走了。 除了路费与粮票,母亲还让他带了四双新布鞋。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母亲做的鞋可以储备着多穿两年。再者,到了特别难的时候,还可以卖点钱换口饭吃。 第一站,尚本礼老师与王臣起来到了陕西铜川,时间是 1962 年的春末夏初。因为天晚,铜川已经没有到县乡的汽车,他们就在一个小旅店住了下来。那时候,对人员流动管理特别严,各地政府都有专门人员稽查“流窜人员”。在小旅店,尚本礼老师与同学被稽查人员拦住。他们拿出介绍信,讲明情况。稽查人员告诉他们,像他们俩这样从全国各地来的人特别多,根本无法收留,让他们立即原路返回。他们的介绍信被收走,等于没了通行证,到哪里都是违法的“流窜人员”,只能回去。 2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