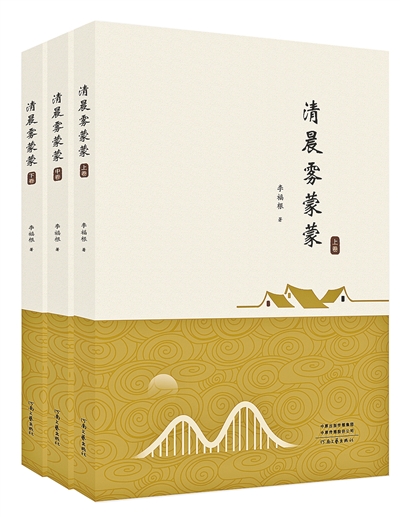|
||||
拴柱看着马桂花忙里忙外的身影,常常暗自思忖:俺算讨了个能干的媳妇。有时他也会拉住桂花粗糙的手,放进自己长满厚茧的大手里抚摸着,桂花总会娇嗔地瞪他一眼:“又没正经了吧。”夫妻俩起五更搭黄昏,秋天割完稻,撒上三亩多田的花草,春天割了嫩花草下锅一煮,搅拌两瓢稻糠,一天的猪鸡饲料全有了。农历四月中旬割了花草晒干后一粉碎,一年的猪鸡饲料大部分得以解决。养猪和鸡屁股的进项,加上自身干木工活的积蓄,硬是凑凑合合盖起了七间房。这两年孩子上学花钱多了,夫妻俩照旧坚守着这条持家路。拴柱到学校问过老师,两个孩子的学习在班里都是前几名。他满心希望孩子们都能考上大学,不再像父辈那样背着太阳、月亮过日子。 刘拴柱推开虚掩着的大门,小儿子占河从偏房门口露出脑袋,小声说:“爸,你回啦,俺妈已经睡下了。” “学你的习吧。”拴柱向占河摆摆手。这孩子正读初中二年级,他不想上灵泉河高中,一心要像占峰那样考县城的高中。真是难为这孩子了,每天天不亮起床,吃完早饭骑上自行车往学校赶,回到家小屋的灯一亮就是半夜。 拴柱看占河轻轻关上屋门,他站在院子里,下意识地看一眼正房西屋的窗户,这间屋是大儿子占峰住的,窗户黑洞洞的一片,不到星期天,房间里怎么会有灯光呢。 拴柱一头钻进了木工房。房内正中放着一个条案,摆放着刨、钻、凿子、墨斗等木工家什,四周堆放着大小木料和几件成型、不成型的木制品。案子的一侧摞起老高的桐木板,这是拴柱按桶的尺寸下好的箍桶料,专门留在夜里用刨子刨光滑。夜里发出的声音响动大,自打跟着大贵老汉学手艺,老人便教他更深夜静时只能干些打线、刨平之类的活。拴柱一手抓过木板放在专用的大板凳上固定稳,一手拿起刨子在木板上来回刨动。 条案上的桐木板刨平后一块块放到地上。木工房的门被推开了,占河轻声说:“爸,我睡了,你也早点睡吧。” “不影响你睡觉吧?”刘拴柱直起腰,看着儿子问。 “我早就习惯了。”占河做了个鬼脸,闪身关上屋门。 地上刨好的木板不断增高,全神贯注的拴柱忘了时间。恍惚间,刘拴柱隐约听到“汪汪”的狗叫。不对,咋会是大黑的叫声? “谁?谁啊……”憨声憨气的声音划破夜空。他太熟悉这喊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占据了拴柱的大脑,他来不及多想,大喊一声:“桂花,快起来!”提起一把锋利的斧头快步冲出大门。 养鸡场内,大黑的叫声惊醒了大贵老人。“呜——呜——”大黑的声音警觉而低沉,接着一声声狂吠不止。刘大贵打开房门拉亮院子里的电灯。看到大贵老汉,大黑昂首冲院外大叫两声,又低头向一个圆圆的东西“呜呜”不止。 刘大贵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麻醉弹”,是专为麻醉狗做的。这个圆东西外面涂着一层猪油,硬壳内是麻醉药调拌的碎肉,狗一旦吃了它,便瘫倒在地任人摆布。前年冬天,二黑也是吃了这东西成了偷狗人碗里的肉。大黑也咬开了硬壳,还没有来得及吞吃被闻声追来的大贵老汉救了一条命。眼下看着那要命的圆东西,大黑“呜呜”的声音里仍带着几分恐惧。 “大,大!”刘拴柱边跑便喊:“大,咋啦?大……” 大贵老汉清楚地听到了儿子的喊声。他正纳闷,院外传来敲门声。 刘拴柱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门口,地上一摊衣服里流出的水,一双鞋也陷进淤泥里,光着脚站在地上,手里仍提着那柄斧子。 “咋啦?拴柱。”刘大贵惊慌地睁大眼睛。 “雾太大,没注意跑掉塘里了。” “快进屋脱衣裳钻被窝里。”刘大贵看着浑身哆嗦的儿子,急忙把他拉进屋内。 马桂花、刘柳叶也赶来了。见丈夫那狼狈样,她心疼地嘟囔道:“大活人掉塘里,咋没淹死你呢。”说着,她急忙回家取衣服、鞋子。哥哥为鸡场遭了罪,柳叶自愧得不知说什么好,慌着刷锅熬姜汤。 天蒙蒙亮,刘大贵左手牵着那头健壮的水牛,右肩上扛着犁,来到湾子西头紧靠大堰的责任田。 这一亩八分田简直和他的命运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这田就是他一家五口人的命根子。1947 年大旱,田里的秧苗眼看着快要旱死了,地主的家丁霸占着大堰不准车水,父亲找那些家丁说理,家丁们蜂拥而上砸了水车。 眼看着秧苗成了干草,悲愤交加的父亲从此一病不起。田里绝收,七分旱地的收成也只有三成。这年冬天,父亲含恨离开了人世。母亲为省下一口萝卜、白菜留给小孙儿,全靠野菜、稻糠充饥。饥寒交迫又染上疾病,母亲和大贵两岁多的二儿子相继咽下最后一口气。稻糠、野菜救了年轻的刘大贵夫妇和拴柱,他们硬是挺了下来。 尽管那是隔朝隔代的事,在刘大贵看来,农民要是离开了土地,就像是塘里的鱼跳到地上——等死。 大贵老汉把犁扎进田里,套好牛,一抖缰绳,那水牛“哞哞”两声,四蹄向后一蹬,两条前腿稳健地一步步向前迈动。犁铧犁开了沉睡一冬的沃土,泥土带着草根、腐叶的气味弥漫开来,刘大贵张大嘴巴,尽情地吸了两口气。 雾,白茫茫一片。田地、水塘、大堰好似包裹在云雾里,看不出本来面目。村庄隐在雾帐中,朦朦胧胧。 水牛不紧不慢地走着回头路,犁铧来来回回犁出翻飞的土地。过去一个人在田里干活,刘大贵总想些眼前和今后的光景。或许因为老了,他时下老爱念旧,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也会从脑子里翻出来抖一抖。第一次和柳林的父亲柳世明相遇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20多年前的1967年?就是的。也是这个季节,下午上工前,生产队长本来派刘大贵犁湾子后面一块大田,他执意让队长改派犁这块田。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土地的所有权虽然不断变更,刘大贵始终对这块田一往情深,只要到这块田里干活,心里舒坦,人也精神。后来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刘大贵宁肯少要二分地,也要坚持换回这块田。 心里一高兴,刘大贵吃完午饭没等吹哨子上工便早早赶着牛来到田头。两个多月天旱无雨,田干了,干得如同龟背样呈现道道裂缝。去年秋割完稻留下的稻茬,虽经一个冬季严寒的摧残,仍在灰不咧呲地站立着。 田种成这样,能指望有个好收成吗? 不灌水浸泡,板结的土地是下不了犁的。刘大贵想着车水灌田,双脚已经向大堰走去。有个人坐在大堰埂上,垂着头,佝偻着身子。那人穿着黑布衣服黑布鞋,上衣的下面分明露着衣兜的一角。走近了,那人依然耷拉着脑袋。 “喂,你咋啦?”刘大贵停下脚步,看着那人说:“堰埂上风大,挪个地方坐吧。” 那人抬起头,五十左右年纪,瘦长脸上胡子拉碴。他看看刘大贵,又前后左右扫了一眼,确认身边只有一人,强笑着问:“老乡,这地方叫什么名字?离灵泉茶场远吗?”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你要去灵泉茶场,还是灵泉河茶场?” 11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