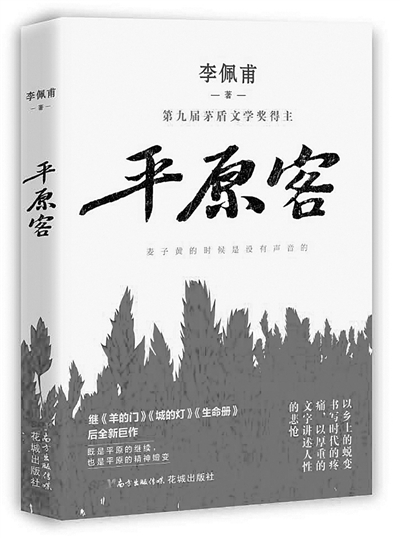|
||||
“罗锅林”这个绰号是人们私下叫的。在白雾笼罩、影影绰绰、人头攒动的浴室里,人们高声喊叫的是两个字:“老林——”或是:“老林,十八号……老林,二十七号……老林,这呢……老林、角里……”于是就有了响亮的回应:“十八号一位!——二十七号一位!角里,三十五号一位!柜前,十六号一位……”随着应声,一条条飞舞着的热毛巾准确地、旋风一般地飞到了客人的手前。 “罗锅林”给人搓背更是一绝。在他这里,“搓背”不叫搓背,他叫“更新”。“罗锅林”给人“更新”的时候,就像是一种表演。那条白毛巾在他手里滴溜溜儿地旋转、飞舞,有时像陀螺,有时像花环,有时像直弓、有时像响箭、有时像绳鞭,不时抖出去,弯回来,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有时他弓着一条腿,有时他拧着脖儿,他的手掌裹在那条白毛巾里,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片红色的印痕。他给人“更新”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捶背”。在他,捶背就像是擂鼓,由上而下、由轻而重,先是雨点似的,而后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后,两掌平伸,起落紧如密鼓,“叭叭叭、叭叭叭叭……”有万马奔腾之势!同时他嘴里还不时回应着各种招呼声:“八号一位——走好!十二号一位——您边上!七号——稍等!” “罗锅林”还负责给人修脚。稍稍闲暇的时候,他提着一个小木箱来到修脚人的床前,在膝盖上铺一条黑亮的垫布,摆上一排有长有短、形状各异、看上去锋利无比的修脚刀,大喊一声:“晒蛋!——”这句“晒蛋”很像是英文,却是要人躺下的意思。等客人躺下来,他会把客人的一只脚高高地举起来,举过头顶,在半昏的灯光下细细地观察、研究,尔后平着放下去,抱在膝盖上,这才下刀…… 在这个热气腾腾的浴室里,“罗锅林”的身影就像是移动着的、半隐半现的“山峰”,不时出现在一个个赤裸裸的屁股后面。这儿,或那儿,喊着、叫着、跳着,麻溜儿得就像是一只窜来窜去的老山羊。他那驼背的峰尖上时常亮着一串明晃晃的汗珠儿,汗珠儿滴溜溜地往下淌,在他背上画出一条条银亮的小溪。他要一直忙到后半夜,等人走光了的时候,他把散落在小木床上的浴巾一条条叠好,这才回到最靠墙角里的那个铺位前,坐下来,喘上一口气。 这个紧靠西边墙角、挨着一个工具柜的铺位,就是他的。这个铺位一般是不卖钱的。现在,赤身围着一条浴巾的花匠刘全有,就在这个铺位上坐着。 虽然已是多年的朋友,花匠刘全有也并不是白住。这时,他已在铺位上摆好了两个黄纸包,一个纸包里是半斤酱红色的猪头肉,一个纸包里是半斤油炸花生米,还有一个锡壶,两个小酒盅。 下半夜,两个朋友,就这么你一盅、我一盅喝着……无话。朦朦胧胧地,刘金鼎夜里起来撒尿,就见刘全有也跟着走出来。他以为父亲也要尿,可父亲没尿。父亲手里端着一茶缸水,走到厕所旁的独轮车前,先是净口,嘴里咕咕噜噜的,把水吐在地上。净口后,再含上水,掀开捂在花筐上的棉被,一口一口地把含了酒气的水喷在花上。父亲说:“这样,花会鲜些。”尿毕,刘金鼎回到浴室,见两人继续喝,还是你一盅、我一盅,酒不多了,抿,无话。偶尔,喝酒的父亲会把一粒花生米顺手塞进儿子金鼎的嘴里。这时的刘金鼎睁开眼,看着两人。在他眼里,这时的两个人,就像是两堆灰。 在童年的记忆里,一年只有一次的洗浴是刘金鼎最高级的享受。正是在开封那个“红星浴池”里,他见识了笼罩在热烘烘的、白色雾气里的、赤裸裸的人生。 于是他认定,“罗锅林”的人生,是卑微的。虽然,那时候,他还不认识“罗锅”这两个字,但意思,他已洞晓。 三 花匠刘全有曾经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这株梅花长呀长呀,越长越高。梅花原本是先花后叶,可奇怪的是,这株梅花却是先叶后花。三叶、六叶、九叶……片片如羽,叶大如扇。长着长着,突然有一天,开花了,花蕊里竟然长出了一个漂亮的妖冶女人。这个妖冶的女子一跃而下,围着他的床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声声叫着:老刘,老刘,我要吃米。老刘,老刘,我要吃米。她围着床转了三圈后,突然,眼里放射出两道耀眼的金光,一下子就把他的双眼刺瞎了! 醒来后,他揉了揉眼,竟然还有刺痛感。这一梦把他给惊住了。他披衣下床,来到院子里,走进花房,围着这株古桩蜡梅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把花刀在他手里举了又举,始终没有落下。 一度,刘全有认为这株梅花有妖气。曾想把它废了。可它的确是太珍贵了。他在它身上花的心血太多,舍不得了。 这棵古桩蜡梅,的确是花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在四川大巴山深处采桩时,虽然在当地也雇了人,但他还是把腰摔坏了,躺在深山的草窝里半天爬不起来。后来他撮土为香,在古树桩前磕了三个头,说:爷,知道您岁数大了,不想走动了。可咱那地界儿阳光好,风水也好。您说您藏在这深山里有谁知道?爷呀,我是想让您天下扬名哪。奇怪的是,自从刘全有愿吁后,再没有出过事故。 古桩挖出来后,还要“晒桩”。桩要晒上三天,去一去湿气,这是怕霉根。在“晒桩”这三日里,那些“胡子”(细小根须)刘全有都一根根地小心梳理好,用土埋上。然后就地在朝阳的山坡上铺一塑料袋,披着一床破被子陪护着。夜晚,星星出齐的时候,湿气就上来了,先不管自己,把带来的塑料布给“桩”围上,等太阳出来时再一一卸去。三日后,“胡子”半干时,先把那条背来的破被子给“桩”裹上,再包上两层塑料布,整个捆扎好,雇人抬下山去。一路上,刘全有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小心。小心。 种子则是刘全有跑到浙江那边的天目山深处采撷的。其实,山下就有人卖。这也不单是为了省钱,主要是想选那些野生的、饱满的、母性好的种子。七月,正是天最热的时候,刘全有赤身穿一大裤衩子,头上戴一破草帽,掂一布袋,再背上一瓶水,在山里攀来爬去地采种。一天下来,人被汗水洗了又洗,腌了又腌,那汗渍都晒成了碱,看上去白花花的,还挂一身的“血布鳞”(树枝挂破的口子)。这一东一西,来来回回数千里。一路上苦哈哈的,餐风饮露就不必说了。 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