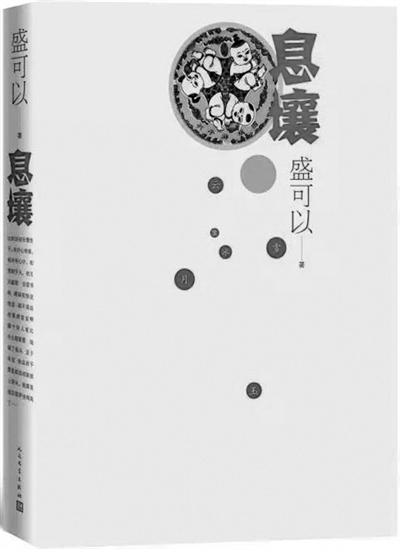|
| 第11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我可以去车站接你,这样你也不用一大早把全小区的人都叫醒了。再说,万一我出差了,你怎么办?初玉不得不切换到方言频道,硬着嗓子说出浑浊的、瓮声瓮气的益阳土话。每次回到以说蹩脚普通话逗乐的乡村,她都不得不隐藏多年外部环境对她的改变。她已是故乡的异乡人。她讨厌方言,听到自己嘴里发出被热汤烫了舌头的声音,她便讨厌自己,但若在不会说普通话的亲戚面前说普通话,她会觉得更加讨厌。如果她实话实说,人们会奚落她忘本,不认得秤,连初云也会认为她嫌弃穷亲戚。她唯一能做的是将方言降调,比如D调降成C调,A调降成G调,可那样一来,她的声音与腔调便透出几分悲伤,显得遥远而淡漠。 我晓得我运气好。洗过热水澡后初云的脸颊是红的,额上发际线偏低,像戴了假发套。你蛮久没有回家了,妈天天盼望你回去。当了主治医师了吗?不聊工作,来了就抓紧时间,下周我当班, 病人多不能陪你,你想去哪些地方?天安门?长城?初玉用的是普通话,避开了方言中奇怪的尾音,这一小动作仿佛在黑屋子里凿了个洞,让她透了口气。 今天是只罩子天哩,初云边嚼边说,还用筷尖指了指外面。她注定是要为方言的流传作贡献的,用浅白的词汇造出生动的形象,没卷舌音,没舌根音,没后鼻音,舌尖上玩弄卵石似的,哗啦哗啦响。但从她嘴里蹦出的有些词汇,初玉已经听不懂了。 “什么罩子天大雾啊,大雾罩子,不晓得等阵会收掉不。”冬眠的方言经过这番刺激练习,这会儿已经在初玉脑子里苏醒,那些关于天气的土腔在耳边响起来。那是奶奶的声音。奶奶是初家的天气预报员,每天早上起床先打开门看天,确定天气之后才开始这一天的日常。她记得什么罩子天、白坨子霜、落凛毛子、飘麻细细、雪只摁。奶奶还紧跟在天气预报后面感叹:啊呀,昨夜里我睡了十个小时。好像她平时少于十二个小时,不慎睡过头似的。奶奶洗脸刷牙,梳头盘发,一切收拾停当,她只需拄着拐杖站门口边打个嗝,放出她胃里的胀气,赖床的人都会立刻爬起来,跟紧一天的节奏。初家都没有一个敢睡懒觉的。 初玉看着初云,后者谈起天气来像奶奶一样自信。当然,没有谁比农民更关心天气,了解庄稼,他们是靠天吃饭的。初玉很早就决定远走高飞,父亲病逝促使她选择了学医——这也是最称小脚奶奶心意的——医生永远不会失业。医学院录取通知书送达那天,戚念慈将玉环交给了初玉,奖励初家第一位大学生,而且是名牌大学。 初玉和初云几乎是两代人,彼此有些生疏。又过了一阵,初玉童年的记忆才被激活,她意识到在那件无形的所谓城市文化外衣的包裹里,体内那个乡下小姑娘依旧鲜活。初云付出很多,自己是得益她的奉献的家庭成员,没理由今天看不惯她乡下人的做派,挑起刺来。 只要天上不下刀子,咱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初玉心里不安,仿佛弥补似的,先到天安门、故宫,晚上吃著名的北京全聚德烤鸭。说真的,我不是来耍的。现在不是耍的时季。初云表情变得严肃,好像现在才言归正传,她勇敢地直视初玉,抿着嘴巴,眼里千言万语。 后者用眼神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我是来做一个手术的。什么病,初玉脸色大变。不是病,我是想。初云说话再次艰难起来,像被硬饭噎住了,我是想复通输卵管。初玉倒没有发出初云幻想的那种尖叫。她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扭头看了一眼日历簿: 二零零零年四月九日 星期六 她走过去,撕下这已逝的昨天。这一天有几个病人情况异常,家属企求的目光像故障灯一下一直在她面闪动。一个家属送她一本书,里面却夹了一个红包——她全部退还。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患者家属养成了不送红包不踏实的心理依赖。他们把这当成生病住院的一部分,还懂得根据医生的重要性分配红包额,连护士都经常收到他们的水果零食。他们不愿承认,这么做将腐蚀人心,红包除了帮助医生品德堕落之外,并不能激活医生潜力,对于医学技术毫无帮助。她因此屡次对科室的护士讲,要耐心,有笑容,要让患者家属信任,让他们相信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初玉将日历扯成碎片扔进垃圾桶,皱起眉头,仿佛她什么地方开始疼。 接着,她去了阳台,拿起撒壶给花浇水。 她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夏天,她放学回家接到跑腿任务。母亲准备了一只老母鸡和半篮子鸡蛋,要她带过去给初云:“她动了手术,特别需要这个。”为防止鸡蛋碰碎,她慢慢地骑着自行车,到初云家时天色已暗。初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小腹袒露在外,上面一条发红发亮的伤疤,脸部因发烧泛着红光,婴儿还躺在怀中吃奶。这场景使初玉深为震撼,好像有东西正在活活残食初云的躯体,而且她很快想到了那些东西就是病痛和婴儿。 应该有人来把婴儿拿走,把病人送到医院。初云仿佛听到她的心里话,平淡地说,没什么大问题,不吃辣椒就好,最后还笑起来 ,一了百了。 初玉以为她的意思是死了干脆,隔了好几年才明白,所谓的 一了百了,指的是男女之事——避孕。这类夫妻间日常的战争,最终以女人的绝育平息。 她脑海里深刻着初云躺在床上,婴儿仍在腋下吃奶的情景,腹部的那道伤口像闪电一样灼目。她想起了阎真清阉鸡时划开的血口。第一次对自己的女性身体产生了恐惧,她没想过女人的身体要承受这些。我永远不要生孩子不要在我生病的时候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吃我的身体。她后来是这么想的,我也不要结婚,不结婚就可以不生育,不生育就不用结扎,死也不要在身上任何地方留下刀疤。 几年后,初玉又目睹了初月结扎回来的情景,这加重了她对身体的恐惧。 姐夫王阳冥拖着一辆两轮板车,他面色黧黑身形矮壮,汗珠从秃顶的脑袋上冒出来,好像淋过雨。他脸上本来就有晦气,人们说他抹过太多尸体,阴气便附上了相貌,上了点年纪之后,整个人就像在死亡液体中浸泡过。他身上佩戴的黄金饰物,倒像是陪葬品——看风水搞活了家庭经济,有钱不知道怎么花,就都堆在身上,重量要盖过别人的,黄金项链往粗里打。他拉着板车,项链与手链沉甸甸的,像一个失去自由的苦隶在长堤上缓缓跋涉。初月躺在板车上,大花被从头捂到脚,一动不动像个死人。 4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