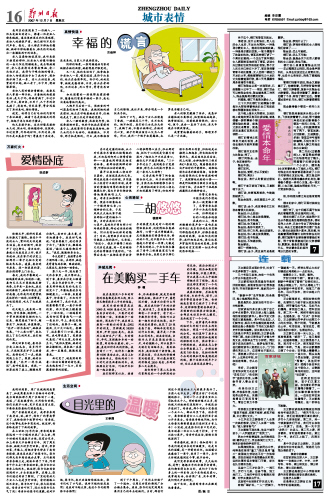|
 |
|
|
|
|||
| 爱情本命年 中原网 日期: 2007-12-07 来源: 郑州日报 |
香茗说,没什么奇怪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不过分为两种,一种是荷尔蒙的主人,能成功地控制欲望;一种是荷尔蒙的奴隶,一辈子摆脱不了欲望的统治。香茗还给柳玎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正处于更年期的女人满面愁容地找到了香茗,诉说丈夫过强的性欲带给她的苦恼。那个女人的丈夫已经五十岁了,却还保持着青春不老的激情。女人仿佛一辆动力不足的火车,每晚都要被马力十足的丈夫拖着勉强行驶,第二天早晨醒来周身疼痛苦不堪言。 柳玎和陈全从第一次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五年了……现在,柳玎完全可以给陈全定性,陈全就是第二种男人,陈全就是荷尔蒙的奴隶。 问题是,柳玎不是荷尔蒙女人。 三十六岁的柳玎此刻满脑子都是孙大那张喷着唾沫的血口和妹妹柳玥那圆滚滚的泪珠子…… 这个晚上是孙大和柳玥,以前的晚上或是给贾正良写的讲话稿,或是领着一群同事挨个楼洞张贴的标语,或是父亲的老胃病,或是欢欢直逼五百度的近视眼…… 柳玎的精神之弦难有片刻的松弛,身体也像块木板样紧绷冰凉。 柳玎推开正在努力的陈全,哭了。 柳玎问陈全:全子,你还爱我吗? 陈全不语。 柳玎还问。 陈全说:爱啊,怎么不爱呢? 柳玎问:真的? 陈全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啊。 柳玎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又重新咽下去了。 柳玎说,你要是真爱我,今晚就别碰我了。 陈全坐起来,坐在黑暗之中,沉默。 柳玎说:全子,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症结。 陈全说:什么症结? 柳玎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陈全说:我不知道。 柳玎说:你不爱我了。 陈全说:是你不爱我了。 柳玎说: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 陈全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柳玎说:我不知道。 陈全说:不知道拉倒。 陈全要走。 柳玎一把拽住他。 柳玎说:全子,我这些天总是做噩梦。 陈全说:梦到什么了? 柳玎说:梦到你把别的女人领到咱们家里了…… 陈全说:怎么可能呢。 柳玎说:怎么不可能! 陈全说:就是全天下的男人都领别的女人回家,我也不能。 柳玎在心里重复着陈全的话……怎么咂摸怎么别扭。陈全是学理科的,从来也没说过这么诗意的话。哼,也没什么奇怪的,狗急了都能跳墙呢。 看柳玎闷着不说话,陈全又重新躺下了,他蜷缩着,只把脊背留给柳玎。柳玎大睁着眼,想象中的陈全也大睁着眼。陈全很快睡着了,睡着之后翻了个身,转到了柳玎这边。借着漏过窗帘的月光,柳玎大睁着眼看陈全。 陈全睡得像个婴孩一样问心无愧。 柳玎轻轻地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飞快地按着键子:此刻,那个道貌岸然的家伙睡得像个婴孩一样问心无愧。不一会儿,手机就噗噗地响了两下,香茗回道:此话新颖,立刻剽窃,多谢!香茗这半年是夜班编辑,不到午夜不下班,夜深人静之时她还在办公室呢! 第二天的《古都晨报》上,香茗果然把柳玎的短信写进了稿子。那篇稿子的倾诉者是一个小伙子,题目是《女友背着我爱上了她的上司》。柳玎对陈全的比喻被香茗篡改成了小伙子对移情女友的比喻。原文是这样的:她若无其事地躺在我的身边,睡得像个婴孩一样问心无愧。我一夜无眠,心如刀割,脑海如那晚的月光,一片荒凉和惨白。 3 姐,你相信夫妻之间还能有爱情吗? 柳玥的家中,柳玎正面对妹妹这样的提问。 柳玎笑了,这个问题不属于你姐我的管辖范围,你还是问别人吧。 柳玥比柳玎小三岁,姐妹两个无论从外貌还是性格都相差很多。柳玥没考上大学,只在中专念了两年财会专业,毕业之后就在教学仪器厂当会计。柳玥比姐姐高十厘米,高且瘦,当她戴着围裙围着灶台转来转去的时候,柳玎就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她的背影,那个背影很像她们的父亲柳顺知,默默地,像是在隐忍着什么,传达着命运的某种难以抗拒的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