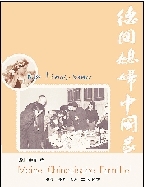|
 |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
|
|
|
||||
“吓!”她的声音更响了,“谁都看得出,这远远超过20公斤的重量。” “那你去拿个秤来称一下吧。”愚谦话里带刺地说,然后就不再理她。她当然没有秤,狠狠地看着我们无言以对,再看看车厢里的人,没有人支持她,没说一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火车徐徐地开进了广州车站,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小李的朋友,他高高地举着纸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关愚谦的名字。愚谦从打开的窗户频频摆手,这个朋友就跟着火车小跑起来,等车停稳后,他立即微笑着上来,帮着卸行李。 “我姓刘,你们叫我小刘好了。”这个年轻人非常友善,长得又高又瘦,但力大无穷,一手拿箱子,一手拿行李袋,很快七件行李就都卸到了站台上。真没想到会那么顺利。不多久我们就已经坐在了当时广州最豪华的东方宾馆里。隔了不久,小刘高兴地给我们送来了两张开往北京的普通快车软席卧铺车票。 当我们来到软卧车厢门口时,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在查票,她的两个眼睛不停地瞄着我们的七件行李,我想,坏了,又该有麻烦了。 “你们这是回家吧?”她微笑地问愚谦。 “是啊。”愚谦回答着。 “好像好多时候没回老家了吧?带那么多东西。” “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全是礼物。” “来,我来帮你们的忙。”说着,她帮我们拿起一件大行李,带我们进入了车厢。 火车准点出发了,分秒不差。那个可爱的女列车员拉开了我们的包厢门,带进来一个新客人,一个穿着军装的上了年纪的人。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你好”就坐下来了。他把他的行李放在门的外面,因为里面可以放行李的地方都已经塞满了。 他一定是一个高级军官,因为我从愚谦嘴里听说,在中国能坐软卧的人不是洋人就是高干,一般的老百姓是没资格坐的。他一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中华牌”香烟,并且让给了愚谦一支。从愚谦嘴里我还听说过,什么样的干部抽什么样的烟,能抽这种中华牌香烟的人大都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现在这个军官吸这种高级烟,职位一定不低。我开始注意起他来了。 这位长者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人显得很慈祥,但愁眉不展,好像心里有不少心事。他一发觉我在注视他,就有点局促不安。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就在愚谦愉快地接过香烟说了声谢谢时,他就有礼貌地问: “您从香港来?” “不,从德国。” “啊! 德国。”他轻轻地点点头,看了看我说:“她是个德国人?” “是的,她是我妻子。” 他对我很不自然地微微笑了一下,又立刻面向愚谦说:“你们到哪儿去?”显然,他这一辈子很少见过外国人,才显得那么拘束。 “回家,到北京去。您呢?” “噢,也回家,去衡阳,”他仔细地看了看包厢的环境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坐特别快车?外国人好像都坐那种车。” “我们当然想坐它,但遗憾的是票都卖光了。”愚谦说。 “特别快车又干净又舒适,让外国朋友坐这种又脏又慢的列车我感到很不自在。” 还没等他第一支香烟抽尽,他又抽出了第二支。我想,坏了,遇到这么一个烟瘾大的,今晚别想好好睡觉了。 “您说得对,”愚谦接着说:“可是把车厢保持干净并不难啊,为什么还要分外国人、中国人呢?外国人应该坐干净车厢,中国人就应该坐脏的车厢?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第二等人了吗?” 这个军官一听愚谦这一番直截了当的话,皱起了眉,开始有些烦躁起来:“您别忘了,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穷和不干净又有什么直接联系,而且中国又不缺人。寻找擦窗户、收拾地毯、清洗被子的人是绝对没问题的吧。谁都知道肮脏和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为什么这一点就改不了?” 愚谦和这么一个陌生人讨论中国火车的清洁问题实在是多余的,而且他说话咄咄逼人,人家怎么受得了。我于是插话说:“其实,对我来说,车厢干不干净都无所谓,只希望火车能开得快一点,越早到北京越好。” 这位军官听我会说中国话大为惊讶,但他不直接问我,而问愚谦:“您的妻子能说中文?” “哦,是的。”愚谦不无骄傲地回答。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