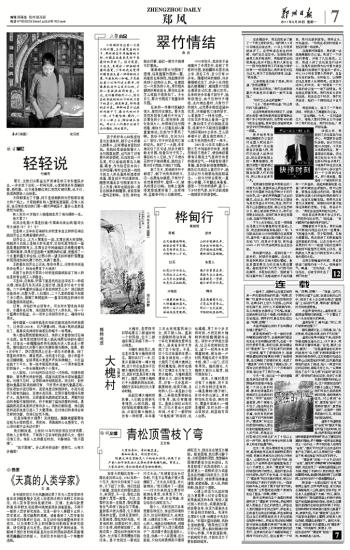|
||||
|
付德芳 那天,当我们从那座庄严而神圣的工字形建筑步出,一步步走下台阶,一时间无语,心里被很多东西触动着,感叹着。记不清是哪位同仁突然打破沉默,说不行,我得再跟铁人合张影。 太阳都显出了宁静,将不是很刺眼的光芒照射在偌大的广场上。大家就都在铁人塑像前面留影,没有人说笑,也没有在按动快门那一瞬齐声喊茄子,蓄在心里的是肃然与钦敬。 铁人年仅47岁就令人惋惜地走尽了他光辉的一生。 他太累了!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这是铁人当年在石油部长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石油会战动员会上充满豪情的诗作。 动员会上,上万人聚集在一起,主席台宽大而简陋,粗糙的大白纸上是粗大的毛笔字,这些毛笔字贴在一面高高悬起的帆布上,主席台正中间端端正正地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四周还竖起数十面飘扬的红旗,便围成了一个庄重的露天的会场,让寒冷的一望无际的被积雪覆盖的荒原顷刻间充满了热烈,充满了激昂。 王进喜在动员会上还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在接下去的五天零四小时的连续奋战验证了铁人的也是所有会战工人的誓言。 不是吗,没有路,积雪下面是坑坑洼洼深浅不一的塔头墩,别说是汽车无法在上面行驶,就是步行也十分艰难。六十多吨重的设备运不到目的地怎么办?他们就把设备拆开,化整为零,人拉肩扛,二十几里的路程不知摔了多少跟头,摔倒了再爬起来……直至在既定的地方将设备重新组装起来。 还有,开钻打井必须有水,可当时水管线尚未部好,水灌车也没有,他们就列成几十人的长队,将一个个盛满水的脸盆,从一双手上传到另双手上,确保开钻用水。 新中国第一口油井就是在如此这般创造条件的前提下,以井深1200米,日产液量8吨,纯油1吨的成果诞生了,真真实实地将贫油落后的帽子一举甩掉。 有人曾经跟我骄傲地说过,他的父亲曾参加过石油大会战。回老家找媳妇时逢人就说他跟石油部长握过手,还拿出一张嘎嘎新的两毛钱纸币送人家说是小意思。媳妇就对大庆那个地方充满好感与期待。结果,都4月中旬了,萨尔图荒原上还是一派冬天的景象,除了零星的井架外,满目荒凉。住的是干打垒,很小的窗子也没镶玻璃,全部用纸从里面严严实实地糊上,干打垒也就十个平方,有一张木板搭的床铺,一个用木板简单钉的箱子,一条长板凳和两个小凳子。 众人皆知,1205钻井队经历过一次井喷。处理井喷事故,首先要关闭封井器,或者往泥浆池中添加重晶石粉。处理不及时,会导致油井彻底报废。而当时,封井器和重晶石粉现场都没有,只好用水泥替代重晶石粉。但在添加水泥过程中,泥浆池里没有搅拌机,水泥与泥浆不能有效融合,至使水泥沉底,这预示着险情将无限扩大。危急时刻,王进喜率先跳进泥浆池里,用激烈扭动的身躯代替搅拌机,终于制服了猛如洪兽的井喷。勇猛跳进泥浆池里的还有许多人。而他们都知道,他们跳进的泥浆池里已混入了大量原油,这对他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伤害,但他们全然不顾。 这是何等的大境界!无须概括。静静地望着那张定格为永恒的图片,用良知,用真诚的心去感受它,内心深处都不会无动于衷! 我们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物资供应还须凭票,而铁人上有母亲,下有四个正在学校就读的儿女,媳妇没有工作。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平静地说“我不困难”。 “我不困难”。多么质朴的话语!感受它,心有太多痛楚!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