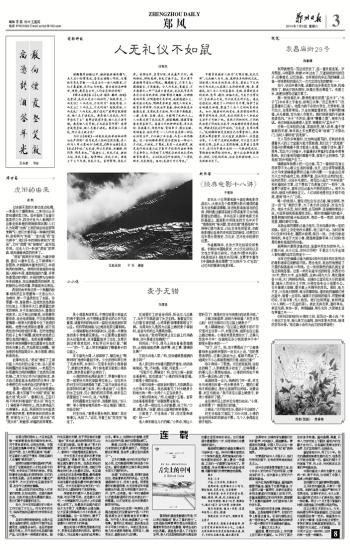|
||||
|
陈勤廉 我早就想写一写这段历史了,但一直未能走笔。岁月易逝,斗转星移,转眼65年过去了,又逢报纸创刊的日子,往事难忘,记忆犹新。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编辑、记者一张张熟稔的面孔又一次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如今,访旧半事为鬼,活着的也多是老态龙钟,风烛残年了,都说夕阳无限好,毕竟已是近黄昏了。伤感之余,我更加想写这篇文章了。 那一张张面孔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孟夫子”。“夫子”口中并非之乎者也,却有口头禅:“反正我来干”(反正是豫东口语)。他是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文质彬彬,语不出众,总是家常话。久坐总编室值夜班,字斟句酌编稿,从无差错,甘为他人作嫁衣。那时刚进城的干部换老婆成风,“夫子”不厌旧,善待“糟糠之妻”,被传为佳话。他这种高尚品德感人至深,被尊称为“孟夫子”! 还有一位年轻的记者,家庭贫困,被人收养,羞于穿崭新的衣服,有件新上衣也要把它弄“枯皱”了才穿出门,当时人都称他“武老皱”。 文人写作多有癖好,比如有站着写的,还有的非抚摸着夫人的三寸金莲方能才思泉涌,我们这个“武老皱”写稿子时要啃着干馍才能进入佳境。他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写出不少好稿子,长篇通讯《幸福》在读者中很有影响。我们看他写稿时啃着干馍,挥笔不止的神态,“武老狗”的外号就产生了。 编辑部年龄最小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批评石油公司领导不关心群众生活的报道,当天,这位领导骑着高头大马来到编辑部要找记者兴师问罪……在省会迁郑大兴土木的省府工地,浪费严重,远从东北运来的红松,经风吹雨打,已经长毛腐烂。他写出小品文“木料诉苦”和长篇批评文章,这下惹恼了负责施工的“一把手”,扬言要下逐客令,宣布这位记者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不为所动,继续为民伸张正义。人们戏称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遂有“陈十八”之称。 唯一的老报人,曾在旧社会当过记者,编过报纸,发过一些“右”倾的文章,为了表示改过自新,改名为左改。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会写相声、活报剧和章回小说,为活跃报纸版面增色添彩。那时他编副刊的稿子,都是把编好的稿子粘连起来,卷成一卷一卷的,放在稿笼里,随时都可交稿。 名扬全城的摄影记者沙老兄,见长绘画并有一定的成就。组织上决定他改从摄影,他二话不说。当时设有《今日郑州》专栏,属图片新闻,每日一张。沙老兄拿起照相机,奔走于大街小巷,爬高楼登脚手架人们戏称他是吃粮标准高的劳动者。 新闻照片最受读者欢迎,适逢中苏友好的年代,人们乘兴说,从今以后,你叫沙莎吧!于是这个几乎全城人都知道的名字沿用至今…… 当年这些编辑记者为耕耘《郑州日报》而忘我劳动的身影继续在我眼前闪现。思念老友,我自然地想起了久居的裴昌庙街29号院。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就生活在这所院落里。这是一所形似庙宇式的院落,东西长约150米,宽约50米,坐东朝西,主房6间为大厅,南北厢房各10间,大门两侧各两间。总编办公室设在大厅的套间里,编采人员按分工不同,分别在各专业小组里办公。冬天靠煤火取暖,夏天靠上天赐予的凉风。那时,电力不足,25瓦电灯照明,每当夜幕降临,值夜班的编辑们移出室外,借着一丝凉风,编排次日报纸的稿件,尽管蚊蝇叮咬,汗流浃背,无人抱怨。他们住则同室,食则同盆(10人同吃一个瓦盆的菜)。彼此无拘无束,直呼其名,亲密无间,亲如一家。其情融融,其乐无穷,大家都生活在幸福之中…… 《郑州日报》创刊65周年之际,我写过一首小诗:“半个世纪又五年,痴儿弄文会庙院,报刊本是无字纸,继续历史写中原。”用这首小诗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吧!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