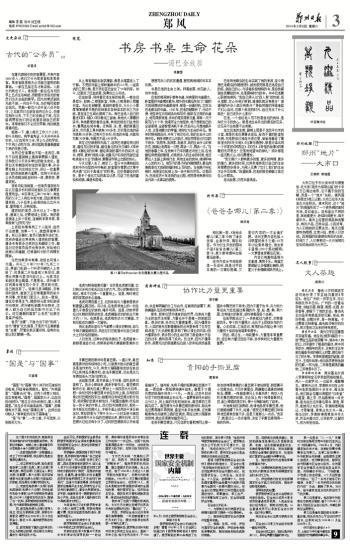|
||||
|
书房 书桌 生命 花朵 ——谒巴金故居 张健莹 从上海淮海路走到武康路,像是从喧嚣走入了宁静。不宽的马路上绿树掩映中的113号,一座英式的三层小楼,是文学巨匠巴金住了55年的家。如今,这里成了巴金故居,免费向公众开放。 巴金故居,保持着巴老生前的格局,一楼依旧是客厅、厨房;二楼是卧室、书房;三楼是假三层藏书室。无论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书,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精装平装的各种版本各种译本的书三万多册,甚至连卫生间也摆满了书。有巴金老人自己的著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有他夫人萧珊的译作,有他最爱的鲁迅全集,有他的朋友们送来的书,曹禺送给他书橱。还有英、法、意、俄的原著及译本,仅仅是工具书就有300多本,仅仅是巴老的译作就有20多种,还有外文书刊、巴老的书稿、书信和文献30多箱,书画艺术品100多件。 现在这些都是陈列品了,连同巴老曾经用过的笔,曾经写过的手稿,曾经看过的《关汉卿》、《祥林嫂》、《娜拉》的戏单,曾经得到的国内外的奖状、证书、绶带,更有“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的死敌巴金电视批斗大会”的通知,萧珊译作禁止出版的协议。 今天这里人去了,楼空了。客厅中彷佛响起巴老和中外访客的开怀畅叙,卧室里好像飘过文革中两夫妻“这日子真难过”的叹息。这些是曾经的历史, 是半个世纪文坛的真实记录,见证了巴老的喜悦和成就,痛楚和苦难。 想想写书人的坎坷遭遇,更觉满房间的书本本珍贵。 书是巴老的生命之渊。拜谒故居,如见故人,如沐书香。 巴老的每间房子都有书桌,书房里的书桌最大,卧室里的书桌摆放最杂,楼外的长廊后来加了门窗的太阳间摆放的书桌最独特,那是一台缝纫机,它充当巴老最后的书桌。1982年,巴老的腿骨折了,行动不便,他坚持在太阳间活动和写作,就趴在这样的书桌上,他写得很艰难,手中的笔变得很沉重,常常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他竭尽全力地坚持,他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是他莫大的幸福,他称它为生命的开花。青年时期他就自问,中年了他还在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晚年他更这么问自己,他总觉得自己付出的不够多,“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在他的垂暮之年,在他有千万字的著述问世之后,在他曾经用燃烧的激情,点亮很多人的生命的时候,他还要在人生路上真诚行走,用他生命的良知,继续叩响人心灵的大门。他写下的是不朽的《随想录》,最后两集就是在太阳间的缝纫机上写完的。当他离不开轮椅时,他甚至在轮椅上加一块木板仍然写。这是因为,巴老经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他觉得他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 巴老用他最后的生命实践了他的承诺,至今想想巴老最后的《随想录》,越发感觉那是巴老挖自己的疮,剖自己的心,与读者肝胆相照的书,是自我解剖自我鞭挞的书,也是震响时代的书。书中巴老撕心裂肺地倾诉:“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身临其境的拜谒者能不扪心自问,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自己该负什么责任? 巴老,一个世纪老人写下的是世纪的良知,是知识分子的良心。那是他生命开出的最后的花朵,这花朵不会枯萎不会凋谢。 走出巴老的主楼,副楼上层是不足四平方米的斗室,那是巴老在萧珊去世后,秘而不宣的卧室和书房,巴老把自己独自关进这里,偷偷地重译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往事与随想》,那是对译出同一个作家的《阿西亚》、《初恋》、《奇怪的故事》的萧珊的无尽思念?还是他绝望中的挣扎?或许那是一座沉默火山,终归要爆发。 “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命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回望故居,巴老的那些肺腑之言还在心头萦绕。 走出故居,仍觉书香绵延。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