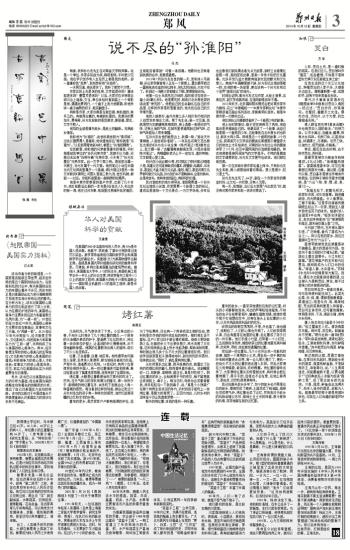|
||||
|
烤红薯 柴清玉 几场秋风,天气很快凉了下来。小区旁边的小巷,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烤红薯的摊点:一个废弃的大油桶改装成的炉子,里面燃了红红的炭火,将红薯一块块架在炉壁上,让温润的炉火慢慢地烤,并不停地翻转拿捏。烤熟的红薯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购买。 红薯,又名番薯、白薯、地瓜等。相传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来传入菲律宾,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要处以死刑。16世纪时,有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人,将一些红薯编进竹篮和缆绳,躲过检查运回了福建老家栽植,逐渐传到了全国各地。 烤红薯,大概是红薯最原始而又简朴的吃法了。然而,在天气转冷的深秋和寒冷的隆冬,捧一块热乎乎、香喷喷的烤红薯在手,尚未吃下肚就会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都会让我这个从农村走出的孩子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忆起那深藏的记忆和浓浓的乡情。 童年的家乡,虽然家家户户都有烧煤的炉灶,但为了节俭费用,还会有一个用砖或泥土砌的灶台,燃料则是农作物的秸秆或捡拾的树枝。那时候生活不富裕,庄户人家过日子都会精打细算。烧柴火把饭做熟之后,灶膛的余火不会很快熄灭,用水浇熄了太可惜,这时母亲就会温上热水洗脸烫脚,帮助消除劳累,有时就会拣几块个头不太大的红薯埋进灰烬。我们放学回到家里肚子饿得咕咕叫,到处找吃的东西时,母亲就会说:“别找了,锅灶里有烤红薯。” 从灰烬里扒出红薯,剥开烧焦的皮,就露出了白色的或橙红色的瓤儿,阵阵香味直扑鼻孔。放到嘴里咬一口,软酥酥、香喷喷、甜丝丝,真是好吃极了。剥过红薯皮的手上,会粘满黑乎乎的炭灰,稍不留意就会抹到脸上、鼻子上。每当这时,母亲总会笑着看着我,用手轻轻勾一下我的鼻子,说:“真是个小馋猫!”在那个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农村的孩子能吃上一块烤红薯,是莫大的享受了。正因为如此,儿时乡村的滋味至今仍让我魂牵梦萦…… 野外的烤红薯,体现的是另一种乐趣。 童年的故乡,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村头的小河静静地流淌,河边的芦苇轻轻地摇曳,不知名的虫子在枯草里低吟,蛐蛐在墙角浅唱,缕缕炊烟不慌不忙地飘向空中,还有在地头上捡红薯的小伙伴,以及共同品尝战利品时的欢乐。 收获后的田野空荡荡的,于是,天也高了,地也阔了,视野远了,人们的心情也开朗了。人们收获得再认真,仍会有遗落在地里的红薯,捡红薯成了孩子们的一件乐事。他们手提小竹篮,还带着一个小钉笆,三五成群结伴而来,随即收获过的红薯地里充满叫喊声、欢笑声,寻找、挖捡那些遗漏的红薯。 挖捡到一些红薯后,几个小伙伴会找一处避风的田埂,掏挖一个简易的小土坑,再捡拾一些干焦的枯叶和树枝塞进去点燃,等一会儿明火熄灭了,便找一些块头不太大的红薯扔进去埋入灰烬。然后大家便在火坑旁唱歌、做游戏,欢呼闹腾。待红薯的香味出来了,大家便将红薯从灰烬里刨出来,有时候会把红薯烤煳了,黑乎乎的,但谁也不会在意,往地上摔两下,剥去皮,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我已经离开故乡多年了,如今的故乡也不再是往日的故乡,草房变成了楼房,土路变成了柏油路,烧柴灶变成燃气炉,烤红薯也成了记忆,然而我对于故乡的风物却难以忘怀,那种土生土长的味道、原汁原味的风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
| 3上一篇 下一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