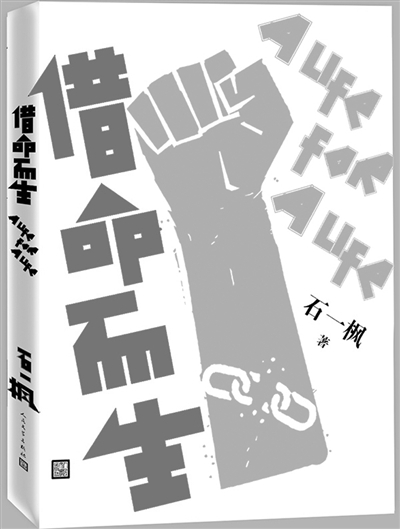|
||||
按照计划,被挑选出来的犯人们要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三到五人。前一组先把货物搬到某个中间地点,替换的另一组再过去接力。一拨儿人干活儿时,其他人就在各自的监舍里候着。如此几趟,等把货物从劳动车间运送到高墙的墙根附近,就该最后一组登场了:他们只需要让货物跨过警戒线,码放在看守所正门内侧的那块空地上即可。而毕竟是要靠近门口,兹事体大,因此对这一组的人员选择是有讲究的。首先,人数不能太多,绝不能超过三个,怕的是人一多就乱,乱了就看不过来;此外,他们还得一贯表现良好,能让管教们“放心”;再另外,不管多么老实的犯人,干多么繁重的工作,只要过了警戒线就必须戴上手铐,这也是不容商量的铁规矩。当一切就绪,管教立刻清场,然后才敢开门,把食品公司的车放进来,让冷库职工自己装货。 如此一来,让姚斌彬和许文革负责最后一段,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姚斌彬虽然手上没劲儿,可许文革干活儿一个顶俩,这就不会耽误约好的交接时间。再说这俩犯人还曾经立过功呢,功臣总是格外值得信赖的。后来上面调查逃跑事件的时候,杜湘东如实交代,如果由他挑人,挑的也会是姚斌彬和许文革。 交代完毕,开始干活。起初一切正常,犯人们或扛或拽,把车间里堆放的麻袋往外运去,远看好像蚂蚁搬家。这些麻袋散放在屋里还不算什那么,聚拢在阳光下,就变成了一座相当巍峨的小山。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长的扁平小木棍组成,就可以联想到北京城里有多少怕热的胖子和馋嘴的小孩儿,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小豆和牛奶冰棍。这还不算最壮观的呢,杜湘东听刘芬芳描述过她们冷库储藏猪腿的场面:几百条猪腿在一字排开的铁钩上齐齐挂着,膝盖微弯,蹄尖笔直,毛发早已褪尽,皮肉覆着白霜,简直像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团正在集体汇演。真不知她怎么会从猪腿联想到芭蕾舞,而猪腿和芭蕾舞都是让她忧愁的。想到刘芬芳,杜湘东的心里便痛了一下,那种痛感倒不剧烈,只是隐隐的,但却让他感到憋闷。这时看到老“杆儿犯”又在偷懒磨洋工,他烦躁地吹起哨子,训斥了几声。 就这样,麻袋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集中再分散,终于移动到了墙根的阴凉处。这时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只好先让犯人们吃饭,吃完饭,杜湘东和老吴才从十七、十八监分别叫出了姚斌彬和许文革。走到劳动地点,杜湘东四下望望,确定附近并无闲杂人等,又低头检查了一下俩人的手腕,确定手铐上好了锁,这才点头,表示他们可以开始干活。许文革弯下身子,两手抓住一个麻袋,硬生生往肩上一甩,直起腰来就走;姚斌彬则左手攥着麻袋角,右手爱莫能助地搭在一旁,屁股朝前捣着小碎步,仿佛一松手就会摔个四脚朝天。俩犯人先后到达了终点,又规规矩矩地折回来,开始第二趟搬运。杜湘东依次看了看他们的脸,都是沉静的、心无旁骛的,仿佛他们并未意识到那道自由与监禁的分水岭近在眼前。随后是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他们沉默地重复着机械劳动,脸上、脖子上淌出了一道一道的汗水,粗布“号服”被渗湿了一片。墙根的小山渐渐瘦了下去,靠近铁门的小山此消彼长地胖了起来。 就在这时,杜湘东想起了一件事。他迟疑了一下,朝几米开外的老吴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要离开一会儿,就一会儿。 老吴叼着烟,大大咧咧地挥手:没问题,走你的。 杜湘东便小跑着穿过看守所,从侧门绕回宿舍,到屋里取了一包东西出来。那是刘芬芳给他织的围脖与毛衣。前两天刘芬芳又打了个电话,交代说,她会在收冰棍棍的日子再“下乡”一趟。这就是督促着他要换东西了。换就换吧,在完成冰棍棍交接的同时,也完成他们这段恋爱的最后交接,真是一举两得。以后刘芬芳就不会来了吧,她会在城里过着她的日子,那些日子将与杜湘东再无交集,她的忧愁也不是他的责任了。杜湘东的心里又是一痛,他提醒自己,一会儿见到刘芬芳,他得尽量表现得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太软太硬太卑太亢了都会招人看不起,作为一名警察,他需要在这种时候保持尊严。他也就剩一点儿尊严了。 于是,杜湘东回去时故意挺直腰杆儿,把大檐帽又正了正。那副样子简直不像是去分手,而是像去立功受奖。围脖和毛衣就夹在腋下,软乎乎却沉甸甸的,谁知道今年冬天就要穿在谁身上了。 然后,他就听见了电喇叭的警报声,紧接着是56式半自动步枪的枪声。声音是从正门方向传过来的,惊得杜湘东浑身一抖。 他撒腿往枪响的方向跑去。 隔着好远,便看见看守所的正门开了个洞。那是镶嵌在大铁门里的一道小铁门,也就一人多宽,平时锁着,只有接收或者释放犯人的时候才会打开。小山一样的麻袋稳稳当当地放在门里,而老吴已经屁股朝天趴在了空地上。姚斌彬和许文革却不见了。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就这么一会儿。杜湘东的脑子嗡了一声,那一瞬间眼睛再看什么都是花的。好在心思还算镇定,他的第一反应是扑到老吴身旁,看看同事是死了还是活着。 老吴身上并无伤痕血迹,只不过迎头挨了一记重击,被打成了乌眼青。杜湘东摇着他的肩膀晃了晃,一道口水从缺牙缝里流了出来。老吴这才叫唤起来:“哎哟我操。” “人呢?”杜湘东吼道。 老吴好像还懵着,叉腿坐在地上,扬手指指敞开的小门。他身上那串钥匙就挂在门上的锁孔里。门外是条土路,通往南边的农田和柏油公路,但土路侧面却有一条河沟,蜿蜒着往东分出岔去,最终会与一条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 杜湘东又吼:“到底往哪儿跑了,路上还是河里?” 老吴说:“没在一块儿,一边儿一个。” 这下杜湘东也懵了。他既没想到这俩犯人居然敢行凶,敢越狱,更没想到他们在行凶和越狱时居然还那么冷静,懂得要往两个方向逃——这样一来,同时落网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而接下来,最让他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当杜湘东冲到门口,站直了往外眺望,心里盘算着该朝哪个方向追时,身后的老吴却结结巴巴说: “枪,枪……” 看守所的管教平时本不佩枪,需要执行重大任务时才佩。而重大与否,就取决于犯人有无失去控制的可能。既然今天是相对自由的室外劳动,因此杜湘东与老吴就都配了枪。枪内共有满匣子弹八发,没拉保险栓。 1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