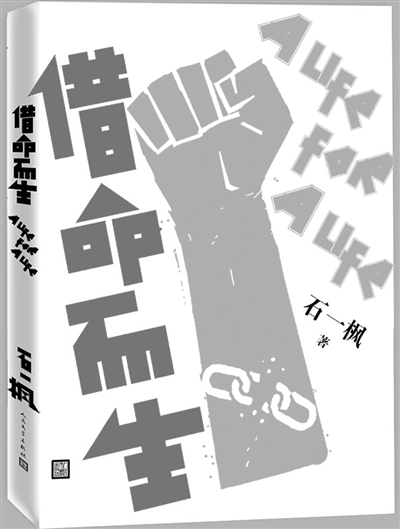|
||||
“希望他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斌彬站了起来,隔着一道铁门,以齐平的高度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已经验明正身的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纪最轻。 偏在这时,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去时,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低头一看,却见姚斌彬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刻,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 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他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姚斌彬显现出了超然物外的专注,忘我地忙碌于这个死刑之前的小小细节。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战士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他们也许把姚斌彬的行为视作了拖延时间或者转移注意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同时弯腰,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算了,时候不早了。” 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与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他是怎么赶往机械厂,怎么上楼进屋,怎么面对面地告知姚斌彬他妈姚斌彬被正法了。他也想不起那女人听说消息之后的反应: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 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XX工程”。囚车先进,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武警方面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下车走进去,目睹或云参观死刑,二是在外面听着,从枪声确认结果。几个送信人面面相觑,没人动弹,杜湘东也没动。于是武警就转身走了进去,关上大门。 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 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人需要补枪。 8 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与惶然,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们又迅速亢奋了起来。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 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个单身汉了,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儿职业的衡量,也从它能否能在价值上实现自己,转移到了它能否能在价钱上养活自己。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所里的车间倒是一直在创收,经营状况却比以前差了许多。象棋子和冰棍棍儿的市场早被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瓜分殆尽,再想上新项目,又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他的“污点”。由于他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 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过去想得没错,刘芬芳嫁给他,说到底是受到了那种上世纪80年代情绪的蛊惑——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这烘托了她心里的浪漫。但几年过去,英雄永无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时糊涂,因此她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还原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现在刘芬芳仍然城里乡下两头跑,平时住在宣武门内,到了周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周末夫妻,小别重逢,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但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略喝一口水,就开始抱怨。抱怨的内容包括她妈脑子糊涂,她爸是个甩手掌柜,她弟弟都是惹祸精,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儿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谁家都快买车了,而她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面的”都舍不得打,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就辣椒酱,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而是挑了靠农田的,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让她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 22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