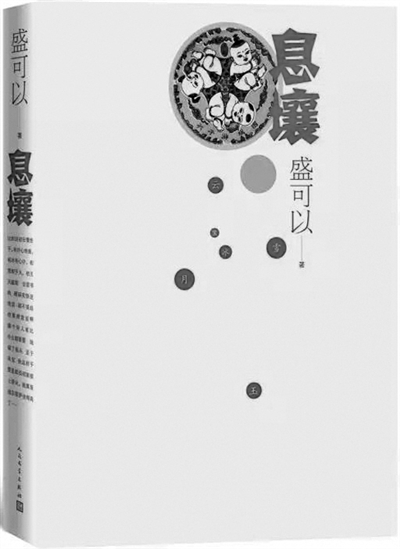|
||||
人们认为这些年老婆子攒了不少钱。也许是预料到某种危机,她来到初云身边,随着锄头的节奏淡淡地说起她过去怎么和她的丈夫相处,是怎么做女人当妻子的,舌头和牙齿磕磕碰碰,夫妻不存隔夜仇。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死了,还不是连片瓦都是你们的。她提到了她的积蓄,数字有点惊人,你要替我保密,清伢子都不晓得的。 初云悄悄瞥她那张满是闪电沟壑的脸,试图将她还原为一个城里略懂皮肤保养的老太太,一个绝不卖掉青菜叶自己吃黄叶懂得生活的女人,但那个惊人的数字干扰了她。她做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那笔钱可以干些什么。她这辈子没有听过那么多钱,想也没想过,像在屋子后面挖出了钱袋,忽然间就发了财。 凉爽的风飘过菜畦,青草和腐叶的味道同时进入她的鼻孔,她在这片土地上的劳作终究不是那么无望,如果拿点钱出来,她的孩子们有机会离开乡间进风漏雨的破教室,去红旗高高飘扬的镇学校读书,上重点高中,考大学。她因此将锄头挖进土里,直起腰来对婆婆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虽然她知道后者一贯对读书学知识有仇,认为文化知识是惹祸上身的东西,对个人并没有好处,她脑子里有时候像被什么东西抽打过,时不时现出些伤痕来,像闪电那样使人惊悚。 她说完立刻后悔跟婆婆讨论这些问题,她很少这么冲动迅速说出内心的想法,阎真清总说她凡事慢半拍像瘟猪不吃食,貌似脾性好,实际上犟得咬狗卵。对于将牲口和她扯到一起他很在行,或者说牲口和妻子是他最了解的两类物种,因此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修辞关联,在她和牲口之间搭上一条无形的线。 她婆婆有些突如其来的情绪,比如扔了锄头离开菜地,我现在还冇死呢?这就要急着将我的口袋翻个底朝天,活活的啃起我的骨头来了。 阎真清听到动静就去了母亲的房间,门虚掩着,他安慰的言语有一阵没一阵像酱菜坛子汩水泡。 初云觉得此刻自己就是荒野的电线杆子,却没人替她感到寂寞,如果不是电线杆太多,便是有善良美德的人太少,杵了那么多年,竟没有一个人来瞟一眼她的孤单。 她继续松土,没有避开蚯蚓,直接将它锄成两截。这条一九九八年的蚯蚓也许当时死了,也许再生后又活了些年头。 第二年,婆婆的生命开始松动,先是糖尿病,后来肾不行,接着整个身体系统运转失常,零部件相继坏掉,从开始到入土,前后不过一年时间,她始终没再提起她的积蓄,那个惊人的数字像她腐烂的器官般失去了意义。 大约隔了两年,初云才知道婆婆的积蓄秘密移交给了儿子,阎真清有次喝高兴了说漏了嘴,但数目减了一半,不知道母子俩谁在撒谎。但这时初云已经不觉得那笔钱有多么惊人,因为这两年她在县城找了份工作,很容易攒出那个数目,那笔钱只能震惊一个挣不到一分现金、有个铁公鸡婆婆且丈夫无能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妇女。 那时阎燕已经读专科,阎鹰在学厨艺,她从家务琐事中挣脱出来,进城做家政服务谋生。最终一家小公司请她专门给雇员做饭,雇员们喜欢吃她做的饭菜,公司和她签了两年合同,还包五险一金。可她一走田地荒了,阎真清也慌了。 他母亲的积蓄他喝酒喝掉了,抽烟抽掉了,偶尔带着那套阉鸡的刑具去更偏僻的地方,运气好的话能阉出半碗鸡公蛋,混上一顿午饭,得几张干不了正事的钞票。四五十岁的人了,眼力不如从前,手脚也不那么麻利,最后一次阉坏了别人的鸡,他知道他再也干不了这个,将这套东西连同破锅烂铁卖给了收废品的。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到自己两手空空,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武功全废,连普通人都不如。他甚至没有把妻子留在家中的能力——他那从酒精中散发出来的低落情绪令他痛苦万分,也找不到那顶孤傲的面具来掩饰心里的自卑,他似乎才真正地认清自己什么也不是。 当初云从城里带回钱财用品,他感到生活不过在以另一种面貌继续,没他什么事。他也不问初云在城里干什么,煮饭做卫生带孩子她在行,死人一样屁股都不扭两下也是她的强项。他心里忍不住要挖苦她几句,也许是嫉妒她那么轻易地就适应了外面的生活,嫉妒她把从城里带回来的战利品交给他时的那种愉快神情。他如果以替荒野的电线杆子都感到寂寞的良善美德对她稍加温存,她下次可能会带回更多物品更愉快。他一面需要她的劳动付出,一面又觉得这些深深地刺激了他的人格与尊严,如果不把她对家庭的贡献理解成一个奴隶对主子的顺服效忠,他简直难以平心静气地忍受下去。 有一天他去城里看她,因为她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他手上也没什么钱了,他会跟她说村里有几家人办喜事,阎家要去上人情簿,每家两百总共恐怕得小一千块,他还会骂他娘的这么多事情偏偏赶到一起,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得回来。他这时的背已经有点弯弓了,过去勾下头阉鸡时留下的毛病,年纪越大越明显,这个使他看起来像个老人。 他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宝马轿车撞翻的。说起来那还是他的责任,在这么宽的街道上躲避汽车对他来说有点难度,因此避开这辆便撞上了那辆。车主马上下来,一边道歉一边问要不要紧,他赶时间开会,如果可以的话,他车里有一万现金,请他拿去,自己到医院处理下伤口,他还留下了手机号码,说有问题随时找他,他会负责到底。 阎真清跌倒没起来,腿上流血,他脑子因受车祸和一万块的惊吓撞击,像地震一样各种板块挪动错位拼接,一团混乱,仍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呆呆地看着宝马车开离视线。他想迅速爬起来,仿佛怕车主反悔,但试了几次才成功站稳,感觉左腿痛得厉害——他知道那是肌肉的痛法,没伤到骨头,地上那摊血仿佛在证明他伤势严重。 他把钱揣到贴肉的口袋里,拧着眉头表情夸张地瘸着腿从围观的人群中一步步跋涉出来,那种艰难缓慢的脚步完全是由于心脏激动的嘭嘭重击导致的——今天早上出门前他预想的只是小一千,现实却是大一万,超出心理负荷,他可以控制面部肌肉,但很难把握心脏节奏。 医院检查结果和他的自我诊断一样没有大问题,消毒包扎时,他腿上疼心里乐,几乎要笑出声来。回家时买了些槟榔烟酒,瘸着腿把初云忘得一干二净。进村见人就发槟榔,那是店主给他推荐的最好的槟榔,卤水不伤口,嚼起来不易碎渣——他平时不吃这东西,纯粹是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一路嚼了回来。 15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