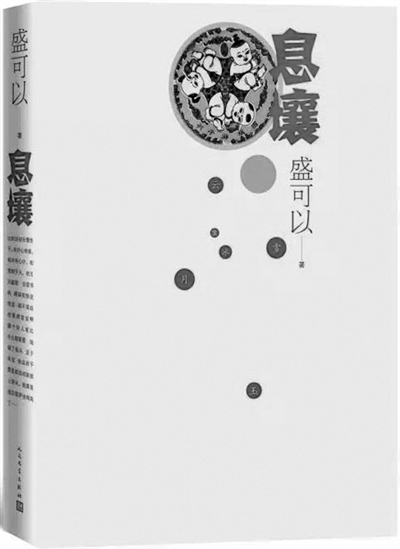|
||||
很难确切分辨他的亢奋是因为一万块钱的刺激还是槟榔的药性,脸上像喝了酒一样发红,连眼睛也像酒精浸泡过。孤傲的光辉重新回到他的脸上。他突然觉得今天晚上不想一个人睡觉,他知道哪根荒野里的母电线杆子和他曾经互相替对方感到寂寞。这没什么难的。他给了她几张百块子,说他本想在城里给她买件衣服,但苦于对她的尺寸一无所知,今晚我特别想好好地量一量你。 那根母电线杆子说她也不知道他的尺寸,连她丈夫的尺寸也记不得了,那死鬼在深圳的建筑工地日搞夜搞,只怕要到过年才能回来。当晚两根电线杆子电线交缠电火闪闪,夜晚就这么不孤单了。 一来二去,总有些门窗不够牢固泄漏光线,走漏风声。他那是拿自己老婆婆辛辛苦苦挣的钱乱搞。初云也是碰哒鬼 ? 最刺激阎真清的便是这种昧着良心的人嚼一些伤他尊严的舌头,他正是听了这样的卵弹琴觉得有必要堵一下他们的嘴。于是他说出那次街上遭遇的车祸,搭帮祖宗菩萨坐得高捡了条命,差点断腿变残废,车主怕担大责任丢一坨钱私了跑了。所以这钱是真正的血汗钱,他流了几碗血换来的。自然,他也不承认那些电光闪闪的夜晚,他从她家后门溜进去,或者她从他家后门溜出来,狗汪汪吠叫时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很早就替初云叫苦,嫁给一个寸事不做的男人,钱不赚一分背底里搞起亲家母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比飞鸽传信还快,初云还没回村,消息就传到她耳朵里去了。 她也没有立即赶回来分个青红皂白,还是平日里慢半拍的性子,等到她认为该回来的时候回来了。很多耳朵侧着倾听她家里传出来的声响,没有摔罐子敲桌子砸碗盆的交响乐,也没有男女高音二重唱,屋子里虚空的地方都塞满了寂静。 人们后来看到初云在园子里撒播菜籽,和阎真清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要他早晚浇些清水,不然到时候不发芽,就得去别人的园子里扯蔬菜吃。有眼尖的人看到她某天早晨进了那根母电线杆子的家门,在里面待了四五分钟后平平常常的离开了。 人们注意到这时的初云连脖子都干干净净的,好像原先积了一层垢进城后全部洗掉了。皮鞋子擦得雪亮,烫了个满发。穿得洋气不过了。于是反过来对初云又有些猜疑,莫不是两公婆都在外边各搞各的,扯个平手,所以不吵不闹。这一假设获得大家的高度赞同,人们心中的疑惑因此也得到了解释。只有卧室里的灯泡闭眼睡觉之后听到黑暗中初云的话。 毛堂客的男人在建筑工地做事,有的是力气。打起人来也是有得轻重,不管死活的,我怕你吃亏。前几天找毛堂客说了,请她帮忙担待点,莫搞出么子乱子来,到时有得办法收拾。 阎真清进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某个晚上比较关键。那晚他坐在自家阶基上,手里打火机火苗一明一灭,眼睛望着进城的方向,表情若有所思。他头顶是半边月亮,满天星星,夜幕就像一块被扎穿了很多小洞的布,光从小洞里透出来就成了星星。他一直想到后半夜,感觉自己的心里也被扎出很多小洞,有些光亮透出来。他跟那根母电线杆子各自杵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再电光闪闪,他固然害怕那个四肢无比发达的建筑工人,但多半因为他心思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城里遍地是黄金,有些人车里的钱像餐巾纸一样,有些人把百块子当零钞,而他还常犹豫着要不要打散一张百块子,因为一打散很快就花掉了。人们都在高档餐馆换口味尝新鲜,而他只是今天吃这个腌菜明天吃那个泡菜顶,多将辣椒炒肉换成肉炒辣椒。人们一有空,就成群结队的出去旅游,而他却窝在这到处是烂泥巴的地方,靠醉酒等着自己的女人口袋里掏几个钱出来喂养他。他越想越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阉鸡阉得那么好,脑壳手指头都那么灵乏,就算是衷于手艺,过于热爱阉鸡事业,也不应该与这个抛弃他的时代为仇。连她这种呆里呆气的榆木脑壳都能在城里头搞得活乏野哒,我也有得么子难搞的。 他第一次想得那么透彻,忽然间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可惜母亲死了,没人可以分享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夜晚与心情——他要进城搞点名堂出来。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睡,不时想起什么,就爬起来做些准备。天亮前他终于睡熟了,做了一个简短的梦,梦见母亲给他买了一件新衣服,竟然和戚念慈的寿衣一模一样。他就此醒来,睁着眼睛琢磨了一会儿,觉得与财运有关,最后认为这个梦表达的意思是母亲不喜欢他去城里,因为城里对她来说就是一介死亡的陷阱。但他不这么认为,自打他轻易地到手一万块之后,他就改变了对城市的态度——虽然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社会变得他都不认得了——他这番进城就是要去摸摸它的屁股,踩踩它的尾巴,和它打打闹闹熟悉起来的。 他沉静了几天,头发乱草般东倒西歪,找出二十多年前的旧衣服,屁股和膝盖磨得放光透亮马上就要破裂的劳动裤,被脚趾头顶穿了的胶底布鞋,背了个烂布袋,塞进一天的水和干粮,收拾妥当后,在初云常用的那块巴掌大的布满苍蝇屎斑的镜子前照了照,只见一个两眼放光的老头舔着嘴皮朝他狞笑。嗯,就这样子,一把老骨头的样子,碰哪里哪里碎。他锁好门,走上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路,他第一次仔细打量周围,发现小河似的沟渠窄得只有尺把宽了,荷塘已成变成了水坑,地球在大口大口地吃掉他过去熟悉的记忆。等到塘坑被垃圾填平了,我也死了。他也觉得地球不经踩,地面比原来塌陷了很多,我肯定看不到地球被踩穿的那一天,他对此并不遗憾。 九点钟的时候,他面对城市主干道快速行驶的汽车,站在人行道上,就像一个从历史穿越过来的人物。不久他来到了上次出事的地方,这里人多车乱,车速很慢。他看准一辆放光放亮的豪华车,忽然从车前横过,膝盖碰到车头跌倒在地,人们围上来,只见他裤腿被刮破,膝盖一道鲜红的血痕。他颤颤巍巍地仿佛惊吓过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在紧张地观察事态进展以便见机行事,只要司机丢一千块钱,多的不想。 越来越多的腿围在四周,他做出呼吸困难茫然无助的样子。人们谴责车主,在主持公道的围观者的帮助下,他得到两千块钱的赔偿。有人要领他去医院看看,他一声不吭相当执拗地拒绝了,带着满怀沉痛的背影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他转到另一个片区,在一个算不上公园的僻静处歇了会,吃了些干粮,决定再上街碰碰运气。这一次遇到的车主是个文着黑眼圈的中年妇女,当他坐在车轮前露出鲜红的膝盖做出疼痛的样子,那女人突然拿出纸巾狠狠地擦掉膝盖的血痕,他完好的皮肤顿时暴露在外,他赶紧爬起来一阵风似的跑了。 16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