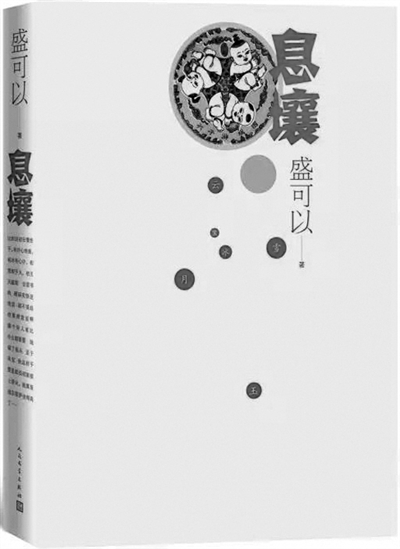|
||||
他的女警官对这件案子做了一个简单陈述,对罪犯的卑劣私径表示鄙视。这些话戴新月听着觉得有点不对劲,旁边人也觉得略为刺耳。他的女警官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看看是否还有别的损失,水也没喝一口就开始捡拾屋子,一边打电话请玻璃店的人过来修补橱窗。烂婚纱直接扔了,能缝补的留下来缝补。 戴新月没有报警,抓进去待几天,出来更麻烦。这种人进监狱就是往脸上贴金,威力更大。一部分人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小镇青年就是这么无法无天,除非出了人命。另有种反对观点,如果完全不给他们教训,他们就会干出杀人放火的事情来。戴新月的女人摆摆手表示算了,要是他们下次来,她要朝他们脸上撒尿。问题是一个小个子女人,怎样完成这种高难度动作,人们散开了,回到家还在想这个事情,多少感觉到那个小个子女人身体爆发出来的威慑力,不知道那些混混们会不会闻风丧胆。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新月影楼这么被砸以后,时运有点背转。也有客观原因,大量的年轻人离开镇子往大城市里发展,在外面结婚买房,镇里的拍摄条件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有的专门去海边或樱花开放的日本,或者埃菲尔铁塔、纽约时报广场,新月影楼再一次面临市场的淘汰,依靠周围的少量需求盘活。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嗅到影楼不同于往时的气息,橱窗里展示着落寞,连店里的石膏模特都透着压抑和郁郁寡欢。 7 初家的五间红砖瓦屋,过去算村里的豪宅傲然独立,周围那些需要猫腰进出屋顶长满野草,下雨时漏雨,刮风时掀顶,下雪时屋顶塌陷的泥砖茅草屋显得十分卑微。初安民死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周围的茅草房不知哪天起全都变成了两层楼房,黑瓦屋顶白瓷砖外墙,有的还镶嵌金光闪闪的亮片。它们反过来包围孤独的红砖瓦屋,像狼群围住猎物,虎视眈眈,带着怜悯与嘲弄的表情;有的地坪上还停着轿车,来去喇叭按得哇哇响,引得人探头观望。这时候初家老屋默默地一言不发,连个人影也难得一见。门口的竹竿上,过去挂满了姑娘们五颜六色的衣裙迎风飘舞,现在只是一根光溜溜的棍子,偶尔搭着一团烂衣破布,那是初来宝的衣服。当他干完香烛先生的活彻底结束一个葬礼,便将衣服脱下来放水里浸一下,搭上竹竿,等下次死了人再穿上。家里七个女人只剩下两个以后,他感觉自己引以为豪的东西消失了,继而陷入一种沉甸甸的愁苦当中。他认为那五个女人离开家,是因为她们不喜欢他了,再也不抱他背他带他去林子里摘野果摘野瓜,不在夏夜里乘凉的时候捉萤火虫,不管荷花开得多么鲜艳都没人来摘一支给他。他几乎都见不着她们了。 后来在奶奶的张罗下,他有了一个叫赖美丽的女人暖床,而且她又生了一个小女人,他以为他们家又会有很多女人的时候,赖美丽却走了,不多久连报时报天气的奶奶也去了她该去的地方。母亲在时他还有口热饭可吃,某一天母亲也不理他了,整天自说自话连瞧都不瞧他一眼,还装作不认识他。他一想起就哭,哭是号哭,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他感到是自己犯了什么错。哭的时间并不长,一两分钟就戛然而止,有时候连眼泪都没来得及下来就停止了;有时候短暂到像婴儿哭前先憋红脸的那一瞬间。所以他身上总是带着某种悲怆的特征,仿佛爱国诗人身上那股浓郁的忧国忧民气质。他的胆子越来越小,除了当他熟悉的香烛先生,打点与葬礼有关的一切,别的什么都不敢碰。人们说他年纪越大越傻,小时候还懂点逻辑头脑也够用,到二十多岁就是一团糨糊,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当姐姐,跟着她去学校上课,在教室外面等她放学。 王阳冥认真地教过他当司公子,学习丧葬仪式,包括殓尸、入棺、请水、出殡一系列风俗习惯,他学得很快,忘得也快,没人引导就出现混乱,顺序颠倒,最后确信他只能当香烛先生。他是一个杰出的香烛先生,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燃烧的香烛,看着它们一点点变成灰烬。他偶尔对司公子唱道场的腔调入迷,但那是耳朵的事情,做法事有几百支香烛需要照顾,他手里紧紧地抓着一把香烛,眼睛不停地在香烛间巡逻。有的人家孝子们哭得地动山摇,有的平淡,有的喜庆,不管孝子们什么表现,他都一样,将来都要去那边,迟早会碰上的,到时候我还是要给他们当香烛先生,他是这么想的,要给所有鬼当香烛先生。 香烛的气味已经渗入他的肌肤。人们闻到空气中的香烛味就知道他来了,或者刚刚经过。刻薄的人说那是一股死亡味,就像他姐夫王阳冥一样,死亡气息也融进了他的面部。但王阳冥会画符念咒,初来宝用什么来抵抗驱逐那些不清不白的东西呢?他有几次倒地口吐白沫,过会儿自己爬起来没事一样,人们才知道他心脏有点什么毛病。 他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像个野人到处游荡,寻找死讯。有时人们发现他在一百公里外的葬礼上忙碌。他就这么在益阳这一带兜兜转转,从不停歇。隔了很久,当人们认为他走丢了或者死在外面了,他又突然出现,头发胡子一堆乱草。连初秀也习惯了他时常消失,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也只像出去的时间久一点。 他当香烛先生当得好,别人需要他,看得起他,他尤其喜欢听司公子喊话:香烛先生,香烛先生,准备好香烛纸钱,现在要到河边请水。他也听见别人说话,但那些话很难钻进他脑子里去,它们就像一些鞭炮纸屑在眼前飞舞,或者秋天的落叶一样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姐姐们一个个离开家,抽走她们带给他的快乐,他也只是困惑地坐在马扎上抠指甲。给他暖床的女人走后,他还是睡在自己这边那边空着。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像别人那样让水从眼睛里流出来。大家通常在春节回来团聚。每个房间里都是人,娃哭娃闹,姐姐们的注意力始终在别的事情,偶尔把目光投向他,也是不咸不淡无关紧要,童年里相亲相爱的日子仿佛不曾有过,娃娃们也是厌弃他的样子,他一走过去他们就哭。娃娃一哭他们的妈妈就会说:“来宝你是舅舅呢?不要和小孩子抢东西。或者,来宝你别抱她,让她自己玩。”他只好呆呆地站着,像一条脖子上系着锁链的狗看着鸡鸭撒欢。 他们不叙旧只聊新,不谈过去只说未来,除了房子车子之类的梦想,貂皮大衣也是追求目标,后来还谈到买马赌博,还有将来儿子娶什么样的媳妇,女儿找什么样的婆家,然后摆好桌子开始相聚的美好时光:打麻将,斗地主,牌噼里啪啦响,这个打错牌捶桌子拍脑袋,那个乐哈哈喜滋滋直把钱往兜里装。 19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