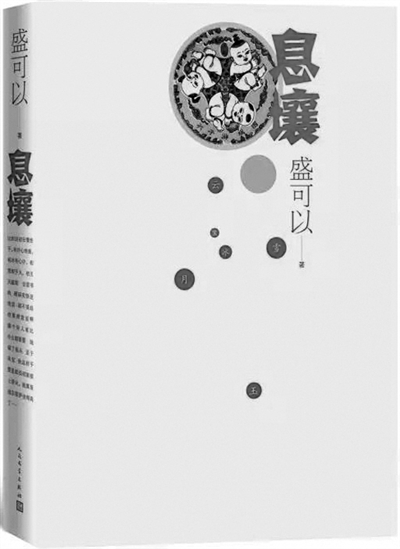|
||||
初云在家只住了一个晚上。白天两人没说什么话,说的也只是与土地牲畜有关。吃饭时也只听见咀嚼、喝汤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响,好像他们在靠咀嚼语言做着激烈深刻的交谈。她放下碗筷后,他还在喋喋不休消灭碗里的饭菜。她做了几道新菜,烹调技术长进了不少,有一瞬间新的口味让他觉得自己娶了一个新的女人,但他一抬头那张旧面孔便粉碎了他的幻象。 他对这张脸谈不上厌恶谈不上喜欢,即便几个月不见也谈不上想念。那晚两个人最终并排躺在床上,中间一道一尺来宽的楚河汉界,他没有出动卒子,她也没出兵,都在自己的地盘上挪动棋步,明明炮可以隔山打牛却按住不动,车可以长驱直入偏偏停滞不前,让蹩脚马跳来跳去。他也许嫌她身上脏了,她也许因为觉得他嫌她身上脏了,这盘棋在黑暗中一直下到深夜,双方均未折损一兵一将,胜负难定,直到一方发出轻微的鼾声,另一方也做出和棋的举动。 她偶尔想到自己那次短暂的激情,对他怀有愧疚:无论如何他蒙在鼓里,他头上戴了一顶有颜色的帽子浑然不觉。有几次她想跟他坦白,但担心坦白带来的伤害,又或者是源于内心深处的那点自私,她不想做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这是她做过的唯一不诚实的一件事。 凌晨她摸黑起床穿衣。她走到大路上时回头看了一眼,低矮的房子像动物一样趴着,窗户还是黑的,整个村庄都在睡梦中。他在黑窗后面看着她渐渐走远,像个监视者那样冷静沉着。这时候她还不知道用不了多久他会出事,而她的人生计划也会因为他的出事而改变。如果她果真像自己说的那样为自己活,她可以不管不顾,继续她崭新的生活与事业。夜里她其实没睡,她想了很多,但什么都没个眉目,也没什么决定。她本来就不是那种有板有眼的人,生活推着她往前走。 10 每到黄昏,吴爱香像戚念慈那样坐在太师椅上,两手平行放椅子扶手,两只脚浸在脚盆里相互搓来搓去,眼睛望着窗外,神色恬淡。春天一窗桃花,柳叶嫩绿遍山竹笋,鸟雀清脆的鸣叫声使时空特别清晰;秋天多数时间阴雨绵绵,冬天也是雨多晴少,不时大雪纷飞,天气陷进泥沼十天半月都不开颜,又落麻细细,村里回荡着戚念慈的声音。 吴爱香看着窗景,然而并不在乎天气因素,甚至像个盲人对所见毫无反应。她那张脸不像六十多岁的女人。女儿们的供养和十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使她增加了体重,脸上肤白多肉,越来越长得像戚念慈,尤其是坐在太师椅里的时候。外地的女儿不断给她寄东西回来,吃的用的穿的,她都整理收好,直到有人回来扔掉发霉的食品,衣服都是新的,她只爱穿那两件旧侧襟外衣。这时上初中的初秀胸脯刚刚鼓起,不懂生理知识,被自己身上源源不断的血吓得要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直到连续旷课两天之后,班主任老师家访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初秀非常欣喜地接受了这一变化,开始迫切地想要变成电视里那样漂亮的女人,红嘴唇、高跟鞋、长发飘飘、亭亭玉立。有一回翻出一双高跟鞋穿了,用画笔描红嘴巴,挺起胸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掠起齐刘海露出高高的额头,变换角度打量自己的脸,眼睛盯着眼睛,撅起嘴巴亲吻镜面。镜子是赖美丽的嫁妆,她生前经常坐在镜前梳头发,死后镜子里没再出现过任何女性,蒙了一层灰。初秀擦了擦镜面,同时也擦过了镜中人脸上的斑点,干净雪白的皮肤看得见青色血管。皮肤雪白是初家人的第二个特征,即便在夏天暴晒变黑了,也会很快恢复。 她将短发梳出中分边分几种不同发型,最后还原齐刘海,头发遮盖额头让她感到安全,好像把自己藏起来了。她这时十二岁,身高一米五五,此后身体到处膨胀,但没再继续长高。十六岁时她变成一个圆润丰腴胸脯雪白的性感少女,眼睛不大但黑亮有神,妩媚流转。她一进初三成绩就垮下来,数理化差得像坨屎,她不以为然,懒洋洋仿佛早早怀春耗尽了她的精力。先是喜欢一个男同学,整天胡思乱想,沉溺于酸甜的初恋滋味。身边无人管教,远方的亲戚鞭长莫及,于是她越来越像匹野母马。有人说她十四岁便丢失童贞,也有的说十五岁,她被一个会唱能弹的做道场的年轻法师在她父母的房间里把她变成了女人。 怪只怪那场法事做了三天,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在人群中相互发现、传情。人们注意到法事做到第二天晚上,道场先生又唱又跳屁股扭得欢快淫荡,像刚上岸的鱼。作为学徒的年轻男孩,这种灵活妖娆的动作充分证明了他在这一领域的表演天赋,跟舞台上的年轻歌星一样魅力四射。 从来没有一次道场会有这么多观众,且多数是妇女,她们出神地观看久久不散,多半是冲着他肉感妖媚的屁股去的,要命的是他还有青春俊美的脸与匀称的身材。他仿佛知道自己的吸引力,舞步灵活妖娆,透着巫气与癫狂,且充满勾引意味。当他每次跳转来扭过身体,便将略含笑意的目光抛向灵堂一角,人们看见那个方向里有初秀,毫无少女的羞涩,也不像妇女们故意隐藏内心的欲望。也许是因为忘我沉浸,她大胆地注视着舞者,眼神随他移动,对面的灯光照着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步入中年的父亲像一块锈铁紧盯着香烛之火,对这空气中飞舞的情欲毫无知觉。他从四五岁开始做香烛先生,对这一行已经熟稔到与香烛之间形成默契,他能从香烛光线的强弱中判断更换香烛的时间,他也能从一炷香散发的烟雾浓淡,知道几分钟后需要更换新香。此时的他已有身经百战胸前勋章累累的将军气度,人群从他的视野里淡化,他的眼前只浮现出死者和香烛,耳朵里只听得见丧乐和法事的演奏唱腔,不再需要司公子焦急地喊:香烛先生,香烛先生,因为他早已经抢在先前准备好了。 人们看不出这对父女有什么相似之处,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人们甚至设想过有什么人替初来宝尽过丈夫的义务,这个世界总不缺乏这样的闲人,他们在暗中窥视,一旦有机会便无所顾忌地做了。又说初来宝说不定还是童男子,他那样子哪里懂得该戳什么地方。有些使坏的瞅机会掏一把他的裤裆,觉得那儿空空的没什么实物。人们总认为自己不带恶意的玩笑制造一点快乐对谁都好。 26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