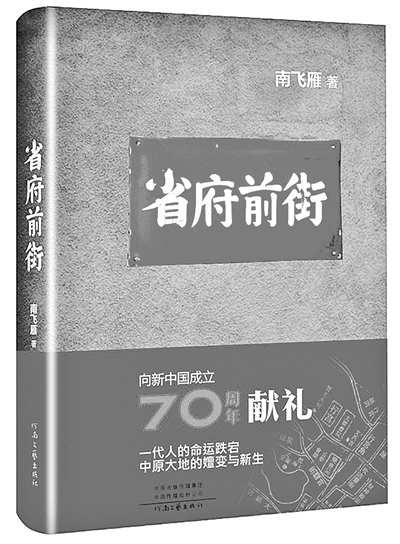|
||||
第一章 娶妇 民国二十五年,沈奕雯十一岁那年,省府前街沈宅出了点事。 事情不大,也不小。奕雯的父亲老沈,把外室冯氏娶进了门。老沈有这位外室之际,奕雯才刚出世,如今十年过去,沈宅上下无人不知冯氏,进门早无新意可言,所以事情不大;不过在进门酒宴上,奕雯朝继母冯氏放了一枪,枪是真枪,弹是真弹,子弹擦着耳朵过去,削去了一个耳垂,耳垂上还有一条金镶璆琳的耳坠,因为见了血,流血的还是新夫人冯氏,所以事情也不能算小。枪响之后,举座皆惊,老沈也惊,但并不乱,出手夺了枪,卸了弹匣。枪被夺走,奕雯却也不乱,黑溜溜的眼珠子一动不动,看着对面的冯氏。而冯氏更不乱,扯了丝帕擦擦脸颊上的血迹,不动声色一笑,继续招呼宾客饮酒用馔,仿佛那耳垂是别人的,跟她毫无干系。 奕雯有枪,老沈早就知道。枪是她母亲的。奕雯的母亲惠葳,三年前出国,半年前来信离婚,老沈复信同意,但只同意了一半,不许女儿出国与母团聚。老沈固然知道奕雯有枪,却不相信她会用;可能也知道她会用,却不相信她会在这个时候用。在老沈眼里,奕雯当然还是个孩子,枪无非是个黑乎乎的玩具,所以这一切必然有幕后主使。惠葳远在国外,可以排除嫌疑;家里家外能当此大任者,又实在是找不出来,而冯氏毕竟刚进门便挨了一枪,势必得有个说法。所以经此一番,待宾客尽欢散去,新妇入了洞房,这洞房就不像是洞房了,变成了审案;审案的当然是老沈,陪审的是冯氏,被审的却不在——老沈端坐于千工床,双目如炬,对空气审来审去,觉得有必要把奕雯叫来过过堂,冯氏却不允,劝道: “她还是个孩子。” 老沈暗喜,半晌不作声,闷道:“孩子?都会冲人放枪了,还是孩子?” 冯氏只好耐心道:“对孩子来说,也就是个玩意儿,她哪知道会要命?” 冯氏时年二十九岁,做老沈的相好已逾十年。冯氏是个聪明人,就算不聪明,十年相处下来,自家男人的脾气性子,也能摸得八八九九。新婚之夜,老沈不肯洞房,偏要断案,意在给冯氏一个说法;或者谈不上给说法,只聊表一下安慰;又或者安慰也不必表,多少算是个态度。毕竟是沈家娶妇,毕竟是新娘子,刚进门就被继女打了一枪,削了一个耳垂,老沈不断断案子,不说说狠话,于人于己都不够圆。而老沈为人处世,力求一个圆满,这点冯氏自然明白,也乐意配合他把话说圆。眼前的情况是,老沈是亲爹,越是亲爹,越要在后娘面前做出大义灭亲的姿态;冯氏是后娘,越是后娘,越要在亲爹那里一副息事宁人的坚持,这样的亲爹后娘才有担待,才能搭伙过下去。其实老沈和冯氏都明白,奕雯打的这一枪,到底是旁人幕后主使,还是她自己一时心血来潮,都缺乏实际意义,审案也是徒有其表;两人心里虽明白,嘴上却都不说。也正是因为你知道,我也知道,你不说,我也不说,所以都觉得默契,觉得对方好,觉得选对了人。于是事情到了这里就又变了,断案不必再是断案,可以变回洞房。 云雨已毕,老沈倒在床头,疲惫一叹,道:“往后,孩子就交给你了。”冯氏便一笑,笑里带悲,悲中含欣,悲欣交集杂糅一起,虽不言,早把话都说尽了。老沈托付过孩子,事情也做圆满了,便由叹转鼾,头一耷拉径自睡去。冯氏替他折了被角,垫上枕头,听见鼾声变弱,这才披衣离床,推开房门,站在一派薄寒之中,怔怔看着周遭的一切。省府前街的沈家宅子,偌大一个四合院,中庭一棵石榴树,十年中她无数次憧憬过,畏惧过,不甘过。如今就驻足正房门口,想到十年既往首尾茫茫,一时间手足无措。 跟前头那位沈夫人相比,如今这位沈夫人差得太多。这点冯氏自己也清楚,所以十年中从不以外室为羞,也从不奢望能取正室而代之,连做个姨太太都未曾提过,远远地躲在双龙巷一处偏宅。而惠葳知道了有冯氏在,不慌不忙打听过她的底细,倒耻于将她视为对手。于是一个战战兢兢,一个视而不见,多年来也算相安无事。如果情势一直如此,倒也不会有冯氏的机会。问题出在老沈身上。他与惠葳成亲日久,且只有奕雯这一个后嗣,心中自然是不甘,有了冯氏之后顿感求子有望,整日深耕勤种,流连不返;不料冯氏十年里除了小产两次,到头来竟是一无所获,倒连惠葳都不如。外室那点事,无论巨细,早有嘴快的下人一一报来,惠葳听罢,越发觉得老沈一番辛苦殊为可笑,可笑之后又觉可悲,为老沈,也为自己。正好幼弟惠茗成年,时值留洋风行,文家送他出国留学,惠葳便一狠心舍下奕雯,陪惠茗出了国,欧游多国经年不归,屡次来信要奕雯出国团聚,都被老沈拦下。夫妇二人隔着重洋万里书信对阵,文言吵过换白话,后来又用英文,吵到第三年头上,惠葳索性一纸离婚书信寄回。老沈虽跟她感情早已寡淡,却也好生暴跳如雷了一阵,最后在信上画了个圈圈,批了“照允”二字;回信第二天,老沈仍是不忿难平,索性通知冯氏准备进门。如此说来,冯氏由外室扶正,不能不说是捡了个大便宜;既然是捡了便宜,就不能太计较那个耳垂;可话说回来,就算是她想计较,又能拿奕雯如何?人家至少还是沈家大小姐,自己膝下空空如也,连个撑腰提气的都没有。 按照常理讲,外室扶正,入主沈宅,胜利者当然是冯氏;不料胜利者还未祭旗立威,就被继女一枪削去了一个耳垂;耳垂减半,无非往后再戴不得耳坠儿,可枪声一响,胜利者的威风便被打掉了一半,剩下一半又发作不得,生生地扼在喉头。本以为老沈会主持公道,说句宽慰的话,怎知他又是断案又是发狠,吹吹打打折腾一夜,连洞房都差点折腾进去,却始终不见实效。原来毕竟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何况这故人还是他唯一的孩子。老沈在唱戏,能搭戏的只有冯氏,看他演了半天,终于看出想把事办圆,就不能放过奕雯;而老沈实际上既想把事办圆,又不想难为奕雯。冯氏并非不会唱戏,之前苦于没有唱本,也没师傅批讲开蒙,不知怎么搭戏;一旦看出老沈的心思,这戏就好搭了。冯氏配合老沈把戏唱完,看他心满意足睡去,明白自己这耳垂没了也就没了,此后再不必提,也不能提,提了就是自己心眼小,做了后母却不懂得宽谅。或许连老沈都觉得,她好歹也做了正经的沈夫人,搬进了省府前街的沈宅,为此损失掉个把耳垂似乎也不算赔本。既然老沈都这么想,她还有何话说?想到这里,冯氏只觉脸颊凉凉,原来不知何时泪水敷面,又风干了。 1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