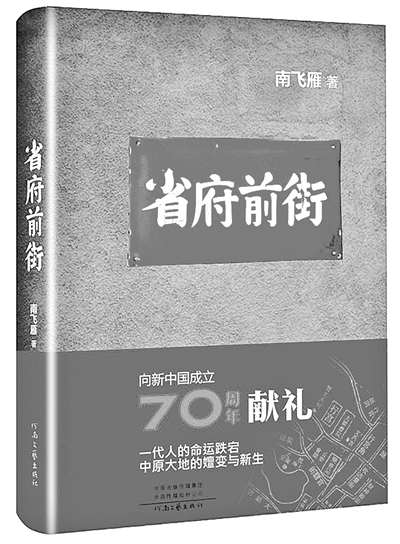|
||||
几个厨子厨娘噤不敢言,冯氏继续道:“这话我不便当面说,你们有谁嘴牙伶俐,给那位老夫人家的捎句话,再有这事儿,就没什么面子可讲了。” 门口却有人拍手笑道:“姨娘说得好,您放心,这话我一定给我环妗子捎过去。” 随着说话声,一个少女飘然而至,朝年长的厨子道:“没听见夫人发火了?反正也喝不得了,端出去倒了吧,眼不见为净。” 厨子赔着笑,却比哭都难看,也不敢应声,低头看着脚背。冯氏叹气,一脸苦笑道:“小姐这是影戏看完了?今天倒回得早。” 奕雯笑道:“我自然还想看的,可人家只给放一场,想看也没有呀!这日本人也真捣乱,占了上海,美国的电影进不来,国片也都是老的,不是《夜半歌声》就是《马路天使》,翻来覆去看多少遍了。还有那些大学生,这么大的雪也不嫌冷,围在影院门口又是游行又是撒传单的,比里头的声音都大。” 本来一屋子压抑的气氛,被奕雯一串连珠炮似的话给轰散了,大家心头都是一松,一个年长的厨娘壮了胆子道:“小姐是不知道,日本人离开封可不远了,说是黄河北全是日本兵。” 冯氏皱眉道:“说这些干吗?小姐忙了一天,累了,先服侍小姐更衣——晚饭好了吗?” 厨子厨娘见冯氏不再提炭的事,暗中都松了口气,正要簇拥着奕雯离去,但见她摆手一笑,道:“我也是好几天没见父亲了,姨娘,您这是要给父亲送粥吗?带我一道吧。” 冯氏倒是一愕。平心而论,她是不愿奕雯去的,这姑娘生就是她的对头,刚嫁进门就被打了一枪,削去了一个耳垂,这两年里奕雯人前人后、开口闭口都叫她“姨娘”,这本是宅门里称呼侧室偏房的,奕雯这么叫显然是存心挤对,时时提醒她出身不正。冯氏不敢当面教训,背地里找徵茹哭了一场,弄得徵茹也觉得礼数不够周全,当即答应下来,要找奕雯说清楚。冯氏还担心徵茹话重,把小姑娘说狠了,惴惴不安了一夜。不料第二天晚上,徵茹兴高采烈来报,说找奕雯谈过了,真是个懂事孩子,叫冯氏“姨娘”根本不是说她出身如何,而是把她和惠葳视为姐妹,惠葳是母亲,冯氏自然就是姨娘,母亲不在身边,姨娘就是最亲近的。冯氏笑得释然,心却凉透,脸上还要装出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其实她何尝不知,小姑娘那些说辞显然太可笑,徵茹当然是不信的,不过可笑与否、信与不信都不重要,他所要的只是一个说法,能自圆其说便好。既然徵茹都故意装糊涂,做和事佬,她再强势去争,又能争到什么?膝下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往后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即便争来又能给谁呢?反正奕雯早晚是要嫁人的,再难也就这几年了。冯氏抱定主意,凡事处处忍让,不跟奕雯计较。既然奕雯要去看徵茹,那就让她去,不然回头落个不让父女见面的名声,更不好听了。冯氏想到这里便是一笑,道:“也好,我刚让人叫了车回来,风大雪大,千万别着了凉。”又扭头对厨子厨娘道:“还愣着干吗?快收拾起来——再弄一个酸辣肚丝汤,一个姜汤,把第一点心馆的灌汤包馏上两笼,随便再弄两个小菜,让小姐先垫垫肚子。” 于是厨房里一阵忙乱,奕雯背着手,笑嘻嘻看着众人。不多时汤菜包子端上,奕雯也不客气,吃了个满嘴流油,嚷着要去看徵茹,冯氏倒是满腹的心事,只略微吃了个包子,便再也吃不得了。这时仆从来报,说车已经到了门口,冯氏差人打电话给中兴楼饭庄,叫了夜宵送到北土街三九四号,这才亲手提了暖瓶,跟奕雯一前一后出门上车。车是美国的扒克牌,后座宽而长,冯氏和奕雯各坐一端,中间像是隔着汪洋大海。从上车起,两人就一直沉默,谁都不发一语。好一阵沉默之后,车停了,原来前边有士兵立了栅栏路障,正挨个检查车辆。冯氏皱眉道:“腊八节还查车?这帮兵什么做的,也真不嫌冷。” 司机老石并不答话,默默地排队等着。奕雯却笑道:“要开会呢!听同学说是好大的会,好多大官都来了,从今天起晚上还要戒严呢——对不对,老石?”老石也不回头,梗起脖子,往后视镜里一笑,露出一嘴熏得焦黑的牙。奕雯就咯咯地笑起来,得意地看了冯氏一眼。冯氏早已习惯,并不跟她置气,无所谓地看着窗外,抱紧了怀里的暖瓶。对冯氏而言,现在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她只盼早点见到徵茹。 老石四十来岁。民国七年惠葳嫁到沈家,陪嫁中有一辆美国产的捷母西汽车,老石当年还是小石,作为司机也一道进了沈家,专职给徵茹夫妇开车。一开就是二十年,车换了好几辆,司机却一直是老石。老石跟徵茹年纪相仿,相处日久,情分自然非同寻常,虽是司机的名头,也跟正经秘书、管家没什么区别,徵茹尚且礼遇有加,沈家上下无人敢稍有怠慢,总行的协理、襄理也是笑脸以待。惠葳出国后,老石百般瞧不起冯氏,便向徵茹辞工,要回山东曹州老家。徵茹自然不肯放他走,慰留了半天,好说歹说才没走成。老石个子不高,有些驼背,开车时神情庄严,脖子总是伸得老长,从背后只看得见肩膀。奕雯打趣,说是位Headless Horseman中文意指“无头骑士”,英国、爱尔兰、美国等国均有“无头骑士”的传说。在开车。徵茹有次听到了,笑得打跌,老石当然不知所云,徵茹怕他忌讳,哄他说Headless Horseman是位洋人好汉,跟中国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老石虽喜,但还有些遗憾,说他是山东人,素来只景仰武松武二郎。奕雯便忙安慰他说Horseman是“行者”的意思,讲的正是武松。老石这才喜不自胜,见人就夸奕雯聪慧、懂得多。奕雯一时兴起,还特意考据了一番,竟跟老石说武松是清河县人,打虎、做官在阳谷县,前头一个在河北省,后一个才是山东省,所以武松根本不是山东人。老石听了目瞪口呆,好几天闷闷不乐。徵茹听说后大为不满,责怪她无事生非,为了安慰老石,他放下公事不办,也好生考据了数日,兴冲冲找老石澄清,说此清河县非彼清河县,武松的清河县在山东、河北和河南三省交界处,归山东东昌府管辖,跟他确是老乡无疑。老石这才转忧为喜。 老石开着车,雪还在下,一点没有要停的意思。老石开得也慢,马达轰轰地叫着,车轮缓慢地轧在积雪上,发出嘎吱的声响。前头路障边,车已排成长队,士兵们早成了雪人,却还是没有丝毫懈怠,查过一辆放行一辆。冯氏等得心焦,忍不住道:“老石,能去说说吗?好歹通融一下——天冷,粥该凉了。” 1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