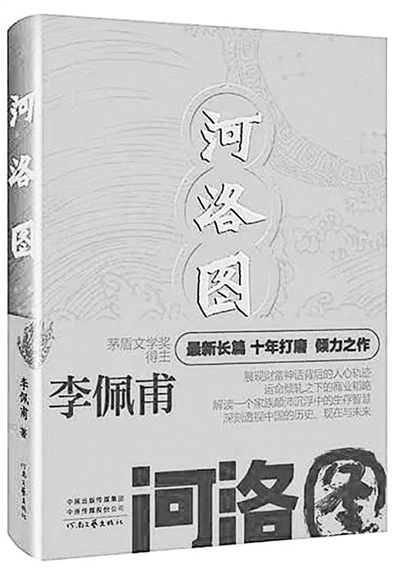|
||||
周亭兰说:这话怎说? 康秀才说:你只要不走。你放心,我走。 周亭兰忙叫道:爷爷。 康秀才说:你想啊,我只要在这个家坐着,就会有人递小话,有人告你的状。一次两次不打紧。可日子长了,说不定哪一天,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信了。我要是信了,你这个家还怎么当? 周亭兰沉吟片刻,说:爷爷到底是读书人。 康秀才叹一声:在康家,不要再提读书二字。 周亭兰说:爷爷,你这么大岁数了,往哪儿走? 康秀才说:这你就不要管了。县学,府学,已请我多次,都被我推托了。吃口饭的地方么,还是有的。 周亭兰见桌上放着一个旧褡裢,一提篮旧书。忙跪下说:爷爷,你说走就走么? 康秀才说:我是当家的,治家无方,还害了儿孙。我出去走走,寻访些故旧,只盼日后能给我康家洗去冤屈。 亭兰说:爷爷,你坐在家里,我也就有了主心骨。你做你的学问就是了。你若这样,让我如何自处呢? 康秀才喃喃道:学问,什么学问?说着,他摆摆手:我主意已定,你不用多说了。 亭兰转身欲走,却又回过头来,说:爷爷,你既把家交给我,不想听听我的章程么? 康秀才摇摇头说:治家的章程不用说。做你的就是了。 亭兰想了想,说:爷爷,你要是真想出去散散心,也行。那你得从前门走。大明其鼓地走。别让人说,是我把你逼走的。 康秀才望着亭兰,久久,说:也好。 第二天一早,当一家老小全起来的时候,只见掌家的爷爷已穿戴停当,走出了堂屋的门。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康熙四十八年的秀才,穿着长衫,却肩一铺盖卷,挎一旧褡裢,提个盛书的小筐,一副出远门的样子。 他重重地咳嗽一声说:我告诉你们,查抄私房是我的主意。我知道你们不服。想想,也有道理。家败如此,作为掌家人,我治家无方,三代人破产读书,却害了我一子一孙。我该当受罚。从今天起,我出门淘口饭吃,以当自惩。从今往后,家中诸事就交给亭兰了。 众人都跪下了,哭着说:爷爷,没人埋怨你呀。你若走了,让我们怎么做人呢? 亭兰这时说:各位伯娘叔婶,掌家爷爷让我告诉各位,昨天充公的“私房”钱,算是家里暂借的。转过年来,等家里日子宽余些,连本带利全部奉还,请各位放心。 康秀才说:罢了。都起来吧。我主意已决,谁也别拦。说完,一步步走出大门,扬长而去。 第 三 章 一 那天晚上,雨是斜着泼下来的。 在黑暗中,那水汽带着嗖嗖、哗哗的响声,一荡一荡地溅在窗纸上,在窗纸上润出了斑驳的、一湿一湿的图案,就像是……带哨的尖钉,或是墨做的泪珠。 在一个孩子的幼小心灵里,关于雨的记忆,就是这些了。那就像是乌云般的黑花儿,一墨一墨地在窗纸上开放,很突兀。它一下子就种在了他的心里。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他也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溅过来的水里,是裹着一股气的。那水也像是有凭借和依仗的,当水溅上窗棂时,就化成了“砰、砰”的声响。是啊,那不是雨。不过,还需要过段时间,他才明白:水是有牙的。 这是康悔文自睁开眼睛之后,上的第一课。 早晨,那是一个春风裂石头的早晨。母亲抱着他,站在了屋门前。那时候他刚刚才周岁,头上戴着虎头风帽,身裹红绒布做的斗篷,穿着虎头棉鞋,露着一张冻红的小脸儿,这很像是一种展览。年轻的母亲就那么站着,一向笑吟吟的母亲脸上有了肃杀之气。于是他看见了水,不,那已经不是水了。泼在屋门前的水已长出牙齿来了。也是过了很久,他才知道:那叫冰。当水长出牙齿的时候,那就是冰。 也就是片刻,母亲的脸上又绽出了桃花。那一刻,他看到了很多人,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齐齐地立在堂屋门前,像是等待着什么。 在他最初的记忆里,女人的脸是一层一层的,就像是庙会上皮影戏里的人物。那些奶奶们、婶婶姑姑们一个个走马灯似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那笑,就有十几种;那声音,也像是用斗量出来的,深深浅浅地埋着点什么;她们声音像是碓碓舀里的石杵,带着一股辛辣的蒜味。 先是二房奶奶荷摇着身子,一摆一摆地走过来,探身捏了捏他的小下巴说:这娃福相。 三房的奶奶颧骨上紧紧地抖出一丝笑,手指头在他的鼻子上轻轻点了一下,尔后又把手伸到下边,扯了扯他的小鸡鸡,说:这娃多喜恰。看看,笑了,笑了。 二房的奶奶也跟着说:笑了。叫个啥,是叫悔文吧? 四房的奶奶眉头一挑,说:这名儿,是当家的起的吧?真格的,那啥。这娃,夜里咋没听见哭啊? 二房奶奶说:不哭好。 三房奶奶也说:不哭好。 这时候,母亲的一只手微微下移,慢慢移到了他的屁股下,尔后捏住了他屁股上的一小块肉,先是摸了一下,像是有些于心不忍,尔后又突然发力,在他的屁股上重重地拧了一把。可是,谁也料想不到,他竟然又尿了。 于是,二房的奶奶说:哎,尿了。 三房的奶奶说:尿了哎。 四房的奶奶说:这孩子,尿人一身。 母亲晃着他,摇着他,抱他的手不由地重了。母亲的手上戴着一个顶针,那个顶针凉凉地顶在他的屁股蛋子上,有点像冰做的烙铁。母亲把他紧紧地揽在怀里,就像是抱着一把尚方宝剑,或是一个可以借重的道具。母亲把他抱出来,是要向人们宣布:我是有儿子的。 可他却尿了母亲一身。 当天夜里,关上房门,母亲解开襁褓,把他浑身上下都捏了一遍,她心里一遍一遍地、战战兢兢地说:儿呀,儿呀,你不会是个呆子吧? 也就是当晚,当母亲重又开门的时候,只见院子里站着几位奶奶。还是二奶奶开口问:悔文睡了么? 母亲说:睡了。 当奶奶们扭身回屋时,四奶奶说:这孩子多好,不哭。 夜里,母亲哭了。她哭了整整一夜,因为她的儿子不会哭。 12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