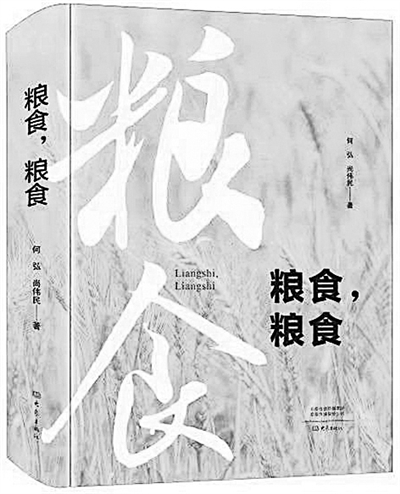|
||||
红薯能不能储存到第二年接上夏粮,直接关系到全家春夏之交“青黄不接”阶段的食物保障和生活质量,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拉回家的红薯,要认真挑选出没有破损、表皮完整的块儿,操作过程中轻拿轻放。储存红薯最关键的,还需要一个好的地窨——有的地方叫红薯窖。挖地窨很讲究,地形,土质,地窨筒的大小、深度都很关键。一般选择地势较高、地下是细沙壤土质的地方,这样可以保持窖内合适的湿度。倘若地势低洼,土质胶黏,透气性不好,窖内湿度过大,红薯容易烂掉。 正常情况下,挖五六米深的直筒,再向两边分别挖高一米左右、宽一米五左右、长两米左右的储藏洞。直筒不能太大,能容下成年人出入即可,否则不聚气,储藏洞进空气多了,就会破坏储藏环境,影响储存时间和质量。太深了,挖掘费工,也不方便人出入,下红薯捞红薯都费气力。 每年下红薯,都是尚学民下到地窨里,窝在储藏洞。大人在地面把红薯拾进篮子或铁桶,再用井绳吊着放进地窨里,尚学民小心翼翼地把红薯倒出来,然后一块一块地由里到外摆好。红薯都是一次下完,一般要连续干三四个小时。地窨里点一个煤油灯,不一会儿煤油的味道就在洞内弥漫开,很不好闻。尚学民窝在灯光昏暗的洞里,不能站,不能躺,只能跪着或趴着,还得不停地把每一块红薯放到储藏洞,每次都会累得满头大汗。 红薯下完,要用透气的玉米秆或草垫子把地窨口盖上,特别冷的时候还要盖得更多些,以防窖内上冻。捞红薯也比较麻烦,每一次下地窨都会弄一身土。到了春天暖和了,地窨内会缺氧,有经验的大人先用井绳吊着空篮子在地窨筒里上下起落,反复多次(这起到了往洞内输送空气的作用),然后才让孩子下去。也有的人忽视了这一点,孩子下去好大会儿听不到动静,等到发现是窒息昏迷了,才知道下去救人。大部分在洞内时间不长、不太严重的孩子都可以抢救过来,也有的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捞红薯的孩子再也没有醒过来。 加工红薯干,比往地窨里下红薯要好一些,但不累是不可能的。母亲用擦床把红薯擦成半厘米薄厚的片,尚学民跟弟弟、妹妹把红薯片摆到院子里和屋顶。红薯干多的时候,也会直接摆在刚刚出苗的麦地里。擦红薯片的擦床与现在厨房用的小擦床原理一样,不过要大很多,一块长二尺左右、一拃宽的木板,中间挖一个长方形孔,嵌进去一个二指宽的刀片,就成了。擦红薯片技术性不高,但也需要小心,总有人不小心擦到手,造成“流血事件”。摆好的红薯片,晒两天还要翻一下。这活很需要耐心。上千斤的红薯片,要一片一片翻个过儿,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干完的,劳动量很大。 晒红薯干最怕遇上阴雨天,尤其是连阴天。连续下几天秋雨,若不及时放晴,淋雨的红薯干就会长毛、发黑、变苦。本来就不好吃的红薯干就更难入口了。 大概是在生产责任制实行前的两三年里,第二生产队家家户户都下粉条。下粉条是人们提高红薯经济效益的办法,其中的劳动量和麻烦, 也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 先打粉。把红薯在水池里洗净,捞出来晾一下,用粉碎机(电动机或柴油机带动)把红薯打碎,存至水泥池子里,再用白棉布把红薯粉末兜起来,以水冲淘,把淀粉冲下去,留下红薯渣。红薯渣晒干可做家畜饲料。沉淀在水底的红薯淀粉要挖出来用白棉布兜住挂起来晾晒,干透后备用。尚学民记得,每年的打粉,要好多天。粉碎机、水泥池都有限, 大家要排队。打粉的每个程序都需要水,到处都是水,人身上也免不了沾水,不光手湿,袖口也是潮湿的。在深秋里,天气转凉,干起活来出一身汗,汗下去之后浑身透凉,被水浸湿的手臂更凉。 下粉条是在冬天结冰的季节,因为那时候做粉条的技术还只能做“冻条”——刚出锅的粉条挂起来后,必须经过冰冻,开化后才能分散开, 否则粉条会粘在一起成为一坨。下粉条的老师儿被称作“端瓢的”,最初是从外村请的,大概一天给一块钱的工钱。后来,为了赶时间,人们发明了不结冰下粉条的技术——做“油条”,即在下粉条的大锅里加入一定量的食油,达到粉条不粘的目的。 在巨大的陶盆里,红薯淀粉加一定比例的白矾与盐,兑温水,通过反复搅拌、摔打,和成软软的、有弹性的面。老师儿把粉面装进专用的铝制漏瓢,以一个与醒木差不多的木块不停地击打漏瓢把儿的根部,便从漏瓢的孔中流出细细的粉条。下边是一个不停烧火的大锅,粉条在开水里煮熟,再捞出来,搭在二尺左右的木棍(被称作粉条杆)上,挂到室外经过一夜的冰冻,在即将开化时拍掉冰凌碴,继续晾晒,干透即成。 下粉条那时候,尚学民年龄尚小,并没有参与多少,顶多就是干点洗红薯、翻红薯渣、拾“粉条头”这样的小活。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干活, 而是吃粉条头。粉条头是制作过程中最初和最末那些粗细不均的短粉条。这些粉条头因为品相差,卖不成钱,只能自己吃。 每年下粉条,都会收获大量的粉条头。母亲便变着法子处理粉条头, 凉拌吃,炒着吃,煮着吃,直吃得到最后看见粉条就想吐。有一次,母亲做挂面的时候放进去很多粉条头。吃的时候,尚学民偷偷地把粉条头挑出来倒到了鸡食盆里。那几年,粉条真是吃腻歪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讨厌吃粉条。 红薯之外,胡萝卜也是那时候农家吃得很多的食物。它很少做菜,经常被煮熟、丢锅充当主食。尚学民对胡萝卜的讨厌程度,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有一次,母亲把胡萝卜切成圆轱辘丢到“糊涂”里,尚学民端起碗一闻到胡萝卜甜腻腻的味道,眼泪就下来了。他不光吃不下去胡萝卜,连它的味道都受不了。 60后的贫苦记忆 1974年,尚学民8岁。对于8岁的孩童来说,世事的艰难尚不太了然,他的关注点,基本都在吃和玩上。 在尚学民的记忆中,虽然饥饿感不太强烈了,但能吃的东西大部分还限于每天的三顿饭,而且都不太好吃,仅仅是填饱肚子而已。那时候, 家里的早晚饭几乎常年不变:红薯“糊涂”,“糊涂”里偶然也会把红薯换成胡萝卜。午饭比较杂乱,或是熬菜配窝头、红薯,或是浓稠的咸“糊涂”(“糊涂”里加盐和干萝卜缨、干芥菜缨、干油菜缨、红薯叶、野菜等),或是红薯干面饸饹,偶尔也吃一顿汤面叶或汤面条。 尚学民的少年阶段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吃的话题。记忆中,很多时候早晚的红薯“糊涂”,红薯很多,“糊涂”却很稀。因为每年分的玉米有限,家庭主妇不敢铺张。稍一松手,玉米就接不上下一年的茬了,只能吃白水煮红薯或红薯干。本家辈分最高的老四爷, 身材魁梧,力大无比,饭量也大。在饭场上,老四爷多次用筷子夹着碗里的红薯轱辘,指着稀得照人影的“糊涂”大声说,啥时候能天天喝上稠“糊涂”,就知足了。 尚学民是在与小伙伴交往时发现不少人家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这让他很不理解,他们家一直都是一天三顿饭的。硬性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把三顿变成两顿,这其中有着多少的无奈。如果不是实在困难, 谁会如此抠门儿呢? 26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