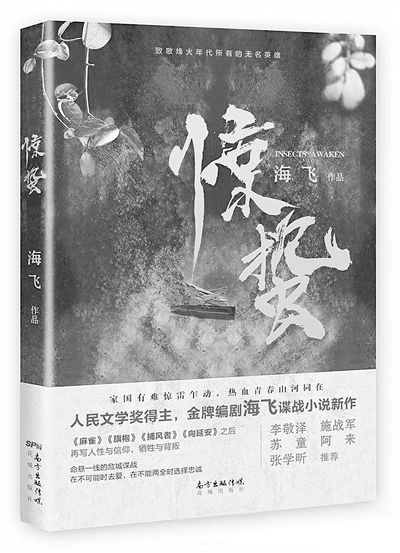|
||||
惊蛰(名词解释):动物入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之为“蛰”。而“惊蛰”即上天以打雷惊醒蛰居动物的日子。此时天气转暖,渐有春雷滚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 壹 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是一个凉薄的清晨。荒木惟坐在窗户边弹钢琴。叮叮咚咚的琴声中,窗口的光线翻滚着漏进来,洒在荒木惟青光光的下巴上。一个钟头以前,荒木惟朝陈山的后脖颈上开了一枪,陈山像一条走路不稳的老狗一样跌扑在地。荒木惟的手在窗口洒进来的光线中低垂着,手里是那把南部式袖珍手枪。他记得在开枪以前,一直在给陈山讲重庆这座完全被雾吞没了的城市。陈山就笔直地坐在那张有靠背的西洋式皮椅上,荒木惟绕着他缓慢走动,边走边给陈山布置任务。他说你接受训练以后,将要去往重庆。知道重庆吗,那个鬼地方的高射炮精准得像长了眼睛。然后荒木惟突然向他后脖颈出枪,陈山几乎是毫无防备地倒下的。开完枪,荒木惟把这支袖珍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面上。与此同时,门被重重撞开,他看到千田英子带着两名日本军医冲进办公室,他们在地上半跪着,训练有素地打开救护箱,替陈山处理伤口。那是一粒斜射的子弹,陈山颈部的伤口已经被贯穿,但没有伤到要害。这时候荒木惟缓慢地走到钢琴边,他坐下来,白而干净的手指头在琴键上按下去。那是一首多少有些忧伤的曲子,他开始在琴声中思念家乡,并且想起了那个充满森林、腐草与木头气息的家乡奈良,以及狭长的号称日出之国的祖国。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冬天。上海虹口区日侨聚集区,一座叫“梅花堂”的小楼。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梅机关。 陈山在恍惚中听到了钢琴的声音,像是溪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潺潺声。他想起了秋天的往事,秋天来临以前,他只是十六铺码头或者大世界门口一名游刃有余的“包打听”。他就那么叼着烟,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宋大皮鞋和菜刀像跟屁虫一样始终跟牢他,他们一起赌博吃酒,插科打诨,在弄堂里勾肩搭背地走路,或者动不动就吼一声,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他们和警察、巡捕、特务还有流氓地头蛇打得火热,如胶似漆,偶尔还为有钱人讨债捉奸。上海遍地流淌着他们的生意,谁给钞票谁就是他们的爷叔。那天在米高梅舞厅的门口,唐曼晴出现在陈山疲惫的视线中,她被一群人簇拥着,从一辆黑色的福特车上下来,向舞厅门口走去。那时候陈山正远远地观望着那个叫威廉的小白脸和黄太太幽会。黄老板的金牙一闪一闪的,他曾经用一根牙签剔着牙,翻了一下白眼对陈山说只要有证据,我就能让威廉死得比白鲞还难看。就在陈山吐掉烟蒂,一脸坏笑地迎向黄太太和小白脸的时候,陈山被两名保镖挡住了。他们以为陈山奔向的是唐曼晴,于是他们同时出拳,陈山一左一右断了两根肋骨。撕裂一样的疼痛,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被完全拆开了,于是他哀号了一声。那次黄老板铁青着脸,站在同仁医院住院部的病床前,并没有给陈山报酬。他说你这个“包打听”不来事的。倒是唐曼晴在第二天让她的保镖赔了他十块钞票。唐曼晴让保镖带话给他,说这是一场误会。 那让我打断她两根肋骨试试?也说声误会赔她十块钞票行不行?那时候陈山从病床上挣扎着抬起头对保镖愤怒地吼了一声。 保镖笑了。在转身离开病床以前,保镖拍拍陈山的肩说,你要敢打断唐小姐的肋骨,那你得赔一条命。你们是不一样的。唐小姐的肋骨你不是打不断,是打不起。保镖说完,手一松十块钞票飘落下来,落在病床上。陈山难过地把头别过去,他其实有点儿无地自容。因为他非常想要那十块钞票。 保镖离开病房的时候,陈山把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轻轻拍了拍,然后对着病房门口骂,婊子。 再次见到唐曼晴的时候,是她陪着一个叫麻田的日本人来米高梅跳舞。那时候陈山的肋骨好得差不多了,他就又松松垮垮地把自己扔在了米高梅舞厅的门口。看到唐曼晴,陈山的肋骨不由自主地痛了一下。唐曼晴踩着高跟皮鞋从他面前像风一样走过,陈山冷笑一声,心里仍然恶狠狠地骂,婊子。 陆军省直属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课课长麻田带了一行人和陈山擦肩而过,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唐曼晴丰腴得有些过分的背影上。麻田身后跟着梅机关特务科科长荒木惟,以及几名刚刚到任梅机关的辅佐官,这些人都是从海军省、陆军省、兴亚院、外务省等机构调过来的人精。麻田就是为这些人精接风的。荒木惟对此不以为意,他根本就瞧不上麻田课长,尽管荒木惟的职衔比麻田更小一些。麻田很瘦,他穿着一件竖条的浅色西装,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只滑稽的蚂蚱。荒木惟看到陈山的时候笑了,他停了下来,说你饿了。这时候陈山才听到自己的肚皮欢叫了一下,陈山不由自主地叼了一支司令牌香烟在嘴上,仿佛抽烟能填饱他的肚皮。荒木惟掏出一只精巧的打火机,替他点上了烟,这让陈山在汽油好闻的味道里有些发蒙。陈山掏出一支烟递给荒木惟,荒木惟摇了摇头说,我从不抽这个。 陈山又听到荒木惟说,你很像肖科长。不,你就是肖科长。 陈山就问,肖……科长是谁。 荒木惟看了身边的助手千田英子一眼,千田英子也笑了,说,一个死人。 然后陈山被打晕了。他都来不及把嘴里叼着的烟抽完。陈山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头顶悬挂着的一盏明晃晃的电灯。他猛地眯起眼,转头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荒木惟。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只麻袋上。荒木惟正在抽雪茄,陈山突然就觉得那雪茄亮起的红色光芒那么的触目惊心。他被两名汉子从麻袋上拖下来,拖到了荒木惟的面前。荒木惟说,给他穿上军装。这时候陈山看到身边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国军军服。陈山在瞬间就被人剥得精光,并且胡乱地穿好了军装。穿军装的时候,陈山看到了许多麻袋包,堆满了这间屋子的四周。他知道自己一定是在一间仓库里。这时候荒木惟顺手把一盏电灯拉了过来,用手举着一只灯泡仔细地看着陈山。强光让陈山睁不开眼睛,灯泡发出的温度像一波波的热浪泼在他的脸上。 1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