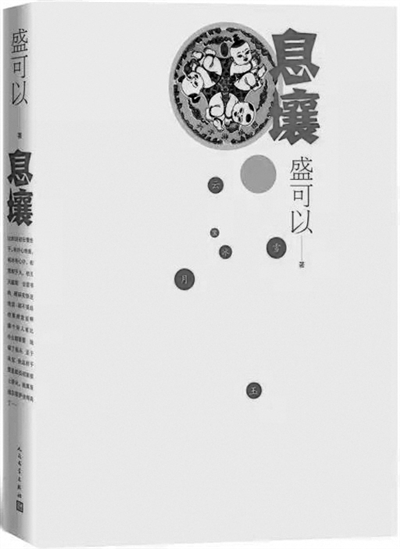|
| 第11版:郑风 | 上一版3 4下一版 |
|
||||||||||||||||
|
||||
2 柳絮飞舞的周末凌晨,北京的天空炸响湖南方言,那种村妇才有的大嗓门撕破了小区宁静,喊的还是初玉的小名。初玉惊起奔到窗前,看见大姐初云站在花园中心,两只手做成喇叭对着高楼喊话。她头发盘成一坨,身穿枣红色的毛线开衫配黑摆裙,喊一声转个方向,身体懒懒散散,动作不急不缓,似乎并不需要谁来应答,她只是练嗓子消遣的——还是那种胖胖的性格。 她是坐那种绿皮火车到的北京,便宜,路上好看风景。好像她通宵没睡,看了一路黑暗,好像北方的黑暗与南方的黑暗不同。她气色不错,肉也没有松垮,二十岁以前生完两胎,按照政策老老实实做了结扎手术,肚皮上留下一条“蚯蚓”,不晓得省了多少麻烦,现在腰是腰,屁股是屁股,一点也不像四十岁的女人。要在城里像她这模样,有点文化,晓得穿衣打扮,正是兴风作浪的好时候。初玉离开故乡的时间太长,到北京上学工作,抛弃方言,完全融入北方城市,疏远了农村生活,也不了解农村女人的变化,她没料到初云来北京要兴起的不是她们乡下湖区的细风鳞浪,而是一场身体的海啸。 上一年五月,初云似乎有心事,回娘家住了几天,什么也没说自己又回去了。大家猜想她对阎真清有些不满,她过去迷上的那双指尖粉红的双手除了阉牲畜什么都不会,挣的钱交给他娘管,地里的活由初云干,经常两腿夹着孩子腾出手来干活,有时夹在腋下,单手炒菜做饭。一开始小脚奶奶便提醒过,乡下人就是靠种田生活的,做得挑得会种地就是顶好的。那时初云完全没想过生活是怎么回事。她想的是那特别粉嫩的手指头,想的是被那样的手牵着走几里地去看露天电影,想的是他那与白玉鞋底般配的孤傲神情,想的是他和她父亲的相像之处,甚至在绿皮火车上,她也没有否定自己当初被十根粉嫩手指吸引的感情。 她在绿皮火车上一路欣赏黑暗,一路回忆,夜窗如镜照着她的脸,时而毅然,时而茫然,时而兴奋,时而兴尽。有一阵她索性仔细端详自己——这窗玻璃镜子比她家那巴掌大的梳妆镜更清晰,更真实。到底应不应该到北京来,答案一会儿肯定,一会儿怀疑。她不知道初玉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她本能地认为,初玉这种大城市里的文化人,态度与母亲肯定不会相同,她从没想过让一个守寡多年的母亲来理解并支持她做那样一件事,她甚至都没有跟母亲聊过那些问题。自打父亲去世,她就成为排忧解难、分担责任的长女,初中毕业就帮母亲喂猪打狗,割禾插秧,照看老小——奶奶虽然精神强悍,毕竟一双小脚生怕踩爆地球似的依赖拐杖,一感冒就咳嗽卧床,一吃辣椒就暗发痔疮,这些都得初云照料。咳嗽和痔疮好说,最难的她每天必洗的小脚——十个脚趾头全部折弯陷进脚板,像贝壳嵌进泥沙,卵石轧进水泥——需热水烫,使劲搓揉,用力按摩,风湿病是这世界上唯一折磨她且让她束手无策的坏东西。其他人都洗过这双小脚,但奶奶只要初云,与其说初云手法好手上有劲,不如说她心里诚恳,做事踏实,性格里没有偷懒耍滑头的东西,她就是这么忠实生活的。 别人说初云惦着小脚奶奶的玉环所以卖力,她倒是喜欢奶奶手上戴的翡翠镯子,奶奶变卖的时候,她心里疼但没吭声。奶奶最终没把心爱的玉环传给初云,而是给了初玉,她一向偏心于她。初云心里不生产嫉妒,安静平和,某些方面就是吴爱香的翻版。别人说她仓促地嫁给阉鸡师傅是逃避家庭,以为嫁出去就能撑直累弯的腰,事实上却弯得更加厉害。这都是人们惯常的思维,事实上,这个问题连初云本人也讲不清。 火车报站暂停时,一个手里抱着孩子挂挎大包小包的女人使初云想起自己生娃带娃的日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学厨的儿子已经到了见到漂亮姑娘心脏擂得嘭嘭响的年纪,女儿阎燕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照样养鸡吃鸡,可不需要阉鸡师傅了,阎真清的手术器具在抽屉里寂寞闪闪,手艺已是生锈的废铁,十根粉嫩的手指早已黯淡无光,也完全看不出它们曾经有过激起女人食欲的辉煌。没人知道他从哪里学会了阉鸡技术,且一心一意用它作为生存手段。 根据他的年龄可以推算出来,他幼年时期到处一片红,红旗、红太阳、红像章、红袖标……他是他妈当下放知青时的产物——这似乎能解释他的指尖为什么粉红鲜嫩——他爸是像墙砖一样老实的本地农民,饥饿时期将最后一口红薯让给老婆孩子,自己饿死了。四年后他妈又嫁给了一坨像泥巴一样老实的本地农民,分田到户后高兴地喝了半瓶白酒掉沟里淹死了——所以阎真清有城里人的孤傲,也又有乡下人的木讷。问题就出在这里,他时常分成两半,自我搏斗,发起狂来像癫子,跟平时那个阉鸡绣花似的斯文男人完全不同。 火车跑得气喘吁吁。初云心里想事,手里剥橘子,机械地往嘴里塞,肥厚的嘴皮默默蠕动。没想清楚一件事情之前,她就一直嚼着,像头牛面无表情。窗外暧昧不清,偶尔几点野光,将黑暗凿出小洞。她不打招呼就来北京,一是不想受任何人的意见干扰,二是反悔了可以悄悄撤退,谁也不知道她有这么疯狂的想法。村里人的习惯是吃了饭嚼舌头消食,对于失败的事物嘴上尤其刻薄——她决不愿那件事落进那些牙缝里塞着隔夜菜的嘴。 过去半年,人们对她的议论已经像大雪压上树枝,她要到北京做一件化雪的大事。她没出过远门,连长沙都没去过,没想到外面那么混乱,兜兜转转跑出一身大汗,终于拿了票上了火车,屁股刚坐稳心里慌意志也摇晃起来。然而火车并不犹豫,一开动就憋着劲一路向北,像怕她反悔似的。 初云洗完澡,换上家居服,喝水,吃早餐。她一进门就讲路上的见闻,在浴室里也扯着调门,活蹦乱跳的方言像不小心飞进屋子里的麻雀东碰西撞。过去初云不是这么聒噪,不得已说起话来,像翻出压箱底的好衣服穿上一样认真。现在她所有的箱子衣柜都敞开了,鸽子离开了笼子咕咕直叫。这是不正常的。她眼神有点飘忽,要么盯着碗里的食物,要么盯着墙上的字画,作出被吸引的样子。她情绪里透露复杂的气息,一方面刻意压制快乐,同时又心事沉沉,似乎随时将抛出一个难题让初玉定夺。 她说她第一次出远门,路上没花什么钱,也没上什么当,所以不知道骗子长什么样子,出门前她就想好了,摁紧钱包,不信任何人,不买任何东西,不管任何闲事,眼睛也只看窗外。 3 |
| 3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