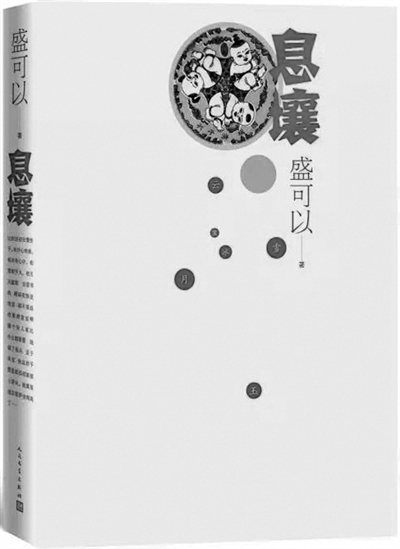|
||||
那天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个陌生男人,他们说他穿着黑皮鞋,一看就是街上来的,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不像是要干坏事的人。她那天甚至没在门口露面,躲在屋子里,时不时看他走了没有。他在长堤上来回漫步两趟,他知道只要村里的人看见他,议论他,就等于她看见了他,知道他来找她了。 她依旧没有再去杂货铺。 他只来过这么一次。过了五年,她再次经过杂货铺,看见里面多了一个女人,还有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她没有碰到过去那发亮的目光。他正在给他的孩子喂饭,用嘴吹凉食物。妻子很年轻,扎着长长的马尾巴,一身干干净净。他妻子看着她走过,像看街上所有的过客一样。 有段时间她猜测戚念慈怀疑她在城里有情况,再也没有要她买过风湿膏药,当她需要什么的时候,直接给钱让孩子们跑腿,给她们钱的时候她出手更宽松。有时候,吴爱香会猜测,也许戚念慈故意给她自由,她才有那样的机会——没什么能逃得过戚念慈的眼睛,她那对几乎不怎么转动的褐色眼珠子嵌在一堆皱皮中,像某种爬行动物。她说的话越来越少,摇头时松弛的肌肉也跟着一抽一抽,她的威严不但没有随着衰老减退,反而在一种迟缓的行动中显得更加坚定牢固,不可动摇。 吴爱香努力忘记在杂货铺干的那件事——准确地说,是忘记肉体在那件事上的记忆,那时她是被肉体包裹的,它挟裹她,她是肉体的奴隶。然而,忘记不过是另一种欲望,它比没发生之前更具体,更真实,因而更受折磨。它打开了另一条感觉通道,那通道离她那么近,不过是五里路的距离。但她被困在一个地方,在与戚念慈气喘声相闻的夜晚,她甚至害怕夜里做与那男人有关的梦。 她不知道是什么在压迫自己,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敢搬出戚念慈的房间,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再找一个男人——在她的意识里,她似乎是赞同戚念慈的,照戚念慈这个模版活才是对的——是她自己协助婆婆牢牢地控制着她自己的肉体——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她将两手揣在腰围兜口袋里,站在阶基上望向田野,算作休憩。此后半辈子,她没有再和任何男人一起使用自己的肉体。她也越来越感觉不到它,它在变得淡薄与微弱,最终气若游丝,这时候她被头巾裹住的头发已经花白。 有人认为婆媳情深,戚念慈一死,她失去了精神支柱,整个人垮掉了;有人说是过于兴奋的刺激导致神经错乱,每天低着头认真地剪纸片,其他什么都不管。赖美丽出事的时候,吴爱香已经不识得人了。她只淡淡地看了一眼赖美丽,接着剪手里的纸片,嘴里喃喃自语,偶尔听得清一些句子,莫到街上去。莫去敲杂货铺子的门,她拿着扫把屋前屋后扫了又扫。 她时常拉着初秀,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初秀总是回答她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她便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电视机成天开着,睡觉也不停。她有时候接听电话,有时铃声响她就用被子蒙住头。大家都知道,戚念慈死后不久,吴爱香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医院取环。我也搞不得蛮久了,到底还是不想做了鬼还带着那个东西,无论如何要取出来。 那天,初云初月初冰一行四人,收拾得干净整洁踏上去医院的长堤,就当是陪母亲做一次春游。 天空万里无云。河边垂柳像雨帘微微漾动。燕子掠过水面。吴爱香裹着浅蓝色头巾,一身藏青襟短衣,双手背在后面,露出罕有的笑容,一路喃喃自语,自问自答。 还是那个鸡埘似的医院,老梧桐被砍了,空地方盖了一栋五层高的医务楼。医务室的日光灯照着雪白的墙壁,像太平间。那个曾经跟吴爱香谈性生活的男医生不见了,替代他的是一个脖颈尚无皱纹的女医生,态度亲切,因为她的母亲也戴过钢圈,只是掉了都不知道,意外怀了她 。 可以说这是一场医疗事故。我妈后来吃草药也没能把我打下来,她说这些时自己哈哈大笑,并且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会诊。上环后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要定期来医院检查。女医生一边开B超检测单,一边悠悠地说:“上回有个患者子宫穿孔,从我们这儿转到大医院去了。” “你查过环吗?”初云问初冰。 “没有。我在市医院上的环,做得很好,医生是我干娘的表妹。” “有亲戚在医院,怎么还真戴那东西,我们村支书的儿媳妇连结扎都是假的。” “村支书的儿媳妇为什么可以假结扎哩?”初月问了一句。 “这就是村支书的能耐。”初云回答,“谁不想躲过这一刀呢。” “我倒是无所谓的。”初月说。也没多疼啊。 “你可别这么说。”初冰打断她。初玉听到会骂人的,她肯定要跟你讲一通身体啊权利啊什么的。想一想,我觉得她说得也对,可我们没办法,对吧 。 女人长了个子宫,这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只想阎燕、初秀她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初云挽起母亲的手臂,打算带她去做B超检查。母亲正盯着着墙壁上的彩色图画。 “那是什么东西?”初云问道。 “图画看上去像一个动物脑袋,耳朵横向张开,仿佛正张嘴大笑。长在你们身体里的。”女医生回答。也是女人最麻烦的部分。 “是肺。”初月说。 “是胃。”初冰说。 “是子宫。”女医生依然很亲切,她站到画前,和风细雨地讲解起来,看这个是子宫口,这一段是子宫颈,这是卵巢,这是输卵管。这一块空地就是子宫。胎儿在这里发育,也是放节育环的地方。 母女四人凑到一块,像一群听到异响的鸡,伸长脖子静止不动,似乎在思考应对措施。 “那东西原来这个样子的啊。”初冰摸着小腹,呼出一口气来。 像朵喇叭花,初月对花有研究,也像鸡冠子花。 初云没说话,她没法想象那是她身体里的东西,孩子是从这一丁点地方长大的。她的视线停在输卵管的位置,思绪万千。 “这个输卵管切断以后,卵子会到哪儿去?”初月问出了初云心里的问题。 卵子遇不到精子的话,过两三天就会衰亡,溶解,被组织吸收,医生回答。 女人们似懂非懂,慢慢走出医务室,好像感觉身体里堆满了卵子的尸体,脚步滞重。 13 |
| 3上一篇 |